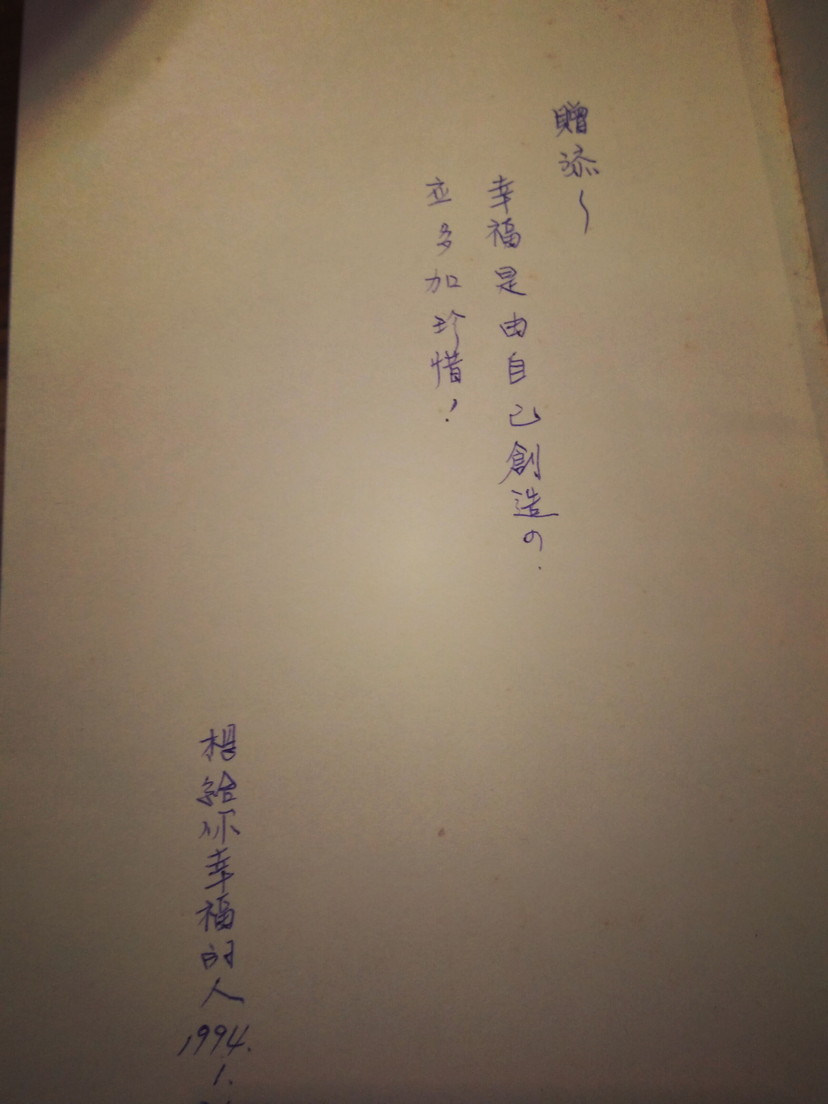當我大口咬下你
已經聞不到你身上永遠揮之不去的貓味了,有點兒臭,卻有份溫馨的貓味。
莎莎留了綠子給你,算是你們熱戀期時甜蜜的負擔。她去美國念書以後,綠子還是你心頭上的肉,就像莎莎一樣。只是她臉書的大頭早換成和一位高帥的洋人,抱著另一隻綠子的合照。或許是對你的另一種補償,是的,那隻雜交而成的美國短毛貓,也被取了相同的名字,只是不知道是否被相同的愛包圍?更多還是更少?
你給我的遠不及莎莎曾擁有的,第一天你就預告我了,當我們在接近高潮那一刻。那種心痛,讓我們同時抵達的高潮更火燙,像瞬間注入喉嚨的龍舌蘭一口杯,整個身體無限縮小在那一個緊縮的部位,大腦已經不存在了,只剩炙熱的痛跟快樂,它們交融在身體的極限上。
你的衣櫃總是空的,行李箱卻老是打理好了一切。有次我覺得請你幫我到寶雅百貨買幾隻牙刷,結果回來後你不自覺先放入行李箱,當時我笑著說你老毛病改不掉,你卻內疚的抱住我,兩個人沒說什麼,就一起大哭,哭完了就做愛,你射完倒頭就睡。我起身去抱住綠子,想哭給牠看,想讓牠內疚,但牠一如往常趾高氣昂,張牙抓了我的手破皮,只好鬆手還牠高貴的自由。總覺得在你的房間,我永遠都不能像你和綠子一樣,融入,不!應該說,連你的行李箱,都比我還受寵。
患得患失的情緒,在一對名義上為情侶,實質上卻是單方面的付出,最能讓人感受的到它壓在胸口的重量。有天我終於忍受不住,把你行李箱的所有家當擺回它們應該存在的地方,你回來的時候並不生氣,只是緩緩的說時候到了,請我離開。
我總想在你無狀態的眼睛裡找到一點,對我觀感的蛛絲馬跡,我多想在你的世界裡看到一點我自己!我想知道你將如何安排我的未來。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並不被容許參與你的未來,只有綠子,只有綠子,和那一堆對莎莎的回憶才能。
那一天我離開了你和綠子,或許你的眼睛還有點不捨,而綠子是完全沒有的,這點多少讓我對過去花在你房間的時間,多了一股恨。
板橋的雨有點大,我走過了府中街,到十字路口買了一袋雞蛋糕,看了看手錶,快十一點了,台北夜晚的街,總會用孤單催促行人回家,回自己的家、愛人的家,或陌生的家。
但那一晚,夜晚的孤單已經趕不走我,我行屍走肉一般步行在接近午夜的街口。從離開他家的第一秒鐘,我就沒停止算過自己的步伐,直到大約走了第六千一百二十步,在某個不知名的路口,在昏黃的路燈下,我看到一位洋人在抽煙,我向前要了一根,他不僅給我一根菸,還想把他那一根粗大的東西塞進我的嘴裡。"Is it made in America?."當知道它的屌是美國製造後,我便開始幫他口交,但我明白,那一刻我正在口交的人,其實是莎莎、莎莎現在的男朋友,和正在房裡收拾衣櫃的那個男人,當美國佬準備要射的時候,綠子在某一瞬間上了我的身,我像牠平日對待我那樣,大力的咬了那男人的陰莖。痛和快感如果真的是一線之隔,我想那一刻他同事擁有了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