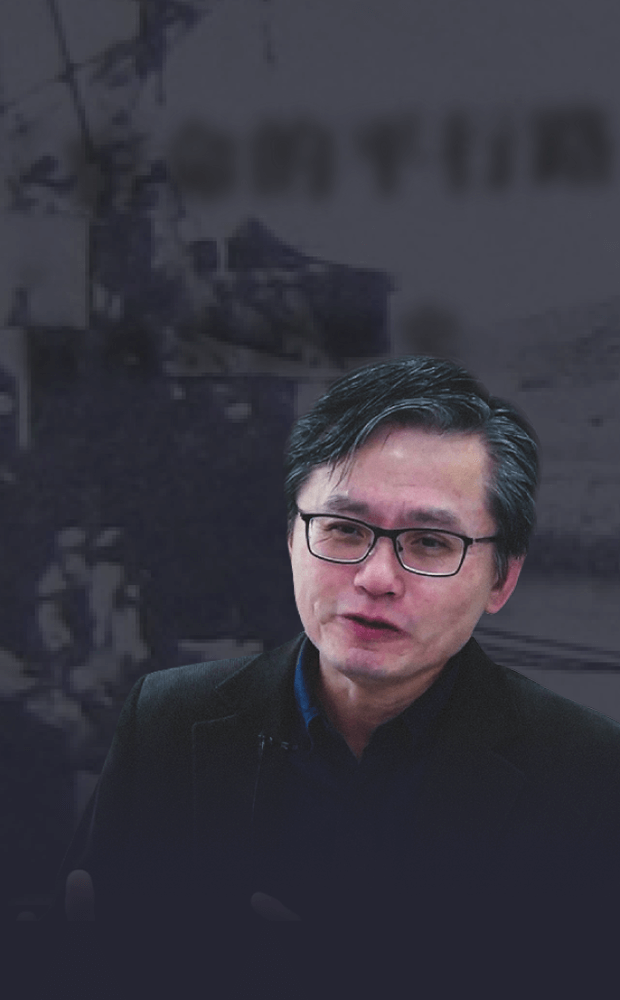「蔣介石把台灣作為反攻基地,從中國大陸陸續撤退到台灣的軍人,當時估計有60幾萬到70萬之多......反攻大陸從來沒有實現,這一批人就長期、幾十年的留在台灣。」指南山麓季陶樓5樓,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福鐘口沫橫飛講述著一甲子的往事,一段這代台灣人熟悉卻又陌生的特殊群體歷史。
「限婚令」種下不安的種子
1952年,蔣介石以總統令頒布全文11條的《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限制現役軍人在營期間不准結婚,即俗稱的「限婚令」,衝擊最基層士兵。60萬來自大陸各省分的軍人,在本該成家的年紀,受限於中央政府維持戰力、毋忘反攻故土的政策,成了大時代的犧牲品,也為往後台灣社會埋下不安的種子。
儘管禁令嚴明,血氣方剛的純樸少年依然嚮往愛情,盼能滋潤空虛歲月。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外省士官兵休假時走入民間,吃飯聚會、從事娛樂活動,自然結識本省女性,甚至愛上台灣女孩。只是在那時代背景下,可能出於經濟因素、家庭因素或文化因素,女方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愛情,「郎有情、女無意,或者是男方以為有意,最後發現只是誤會。」
另一常見現象是感情詐騙。李福鐘曾在國防部檔案中讀到一大批軍法判例,外省男性在娛樂、特殊營業場所認識了台灣女性,以為邂逅了美好春天,沒想到對方拿了錢就避不見面,甚至就此人間蒸發,不諳世事的他們成了愛情詐騙的受害者。
這些外省男性是職業軍人,回到部隊裡頭能接觸軍械,有槍枝、手榴彈,本該用來保家衛國的武器,卻成為他們回到民間報復的工具。在戒嚴時代,軍人攜械殺人幾乎是唯一死刑,「我在國防部看的檔案是上百卷,幾乎每一卷裡頭都有這樣的case(案件)......數量之多,讓我感覺到當時確實是一個問題。」
外省少年變中年
婚姻市場的弱勢族群
歲月流逝,「限婚令」經修改和放寬,在1959年(民國48年)時更名為全文16條的《戡亂時期軍人婚姻條例》,這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已將近10年,理論上外省軍人可以結婚成家、落地生根,但最現實的問題是,他們找不找得到對象?
「我看過一個大概的數字,當時在外省人圈子裡男女比例大概是1.6多比1。」換言之,以當時約120萬大陸人到台灣,裡頭的女性不到50萬人,男性卻高達70多萬,就算倆倆能完美配對,仍有20多萬外省男性必須到台灣民間裡頭找尋婚姻對象。
從政治上來看,台灣社會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原本就有部分本省人對外省人有著相當不愉快的歷史經驗,甚至是仇視。另一方面經濟條件也是大問題,外省軍人獨自來台、舉目無親,當兵薪水又不高,基本上沒房產、財產少,僅有同鄉朋友很多,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自然難得到青睞。
「台灣的家庭嫁女兒,習俗是要有聘金的。」外省軍人在經濟條件上比不過一般的本地男性,就算女孩嚮往的是西方自由戀愛,仍難擺脫原生家庭的影響。經濟、歷史和文化錯綜交織下,一定比例的外省男性一輩子都沒辦法結婚,或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弱勢,成了台灣1970、1980年代的社會現象。

同是天涯淪落人
1983年國片《小畢的故事》上映,主角小畢的父親(實為繼父)正是外省軍人,大時代的種種因素導致他在服役期間沒能成婚,直到退伍後存了點積蓄,終於可以「討老婆」,但在婚姻市場中能選擇的對象十分有限,劇中安排他找了離過婚、帶著小孩的本省女人。
1984年《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上映,主角「莫占魁」(老莫)是退伍的外省軍人,劇中忠實呈現當時的社會情境,他同樣拖到年紀很大了才有機會步入婚姻,對象是當時較弱勢的原住民女性。
「這個現象出現在1970年代以後,這批老兵也都40好幾了。」李福鐘說,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已被趕出聯合國,反攻大陸無望,不少軍人陸續退伍,回鄉之路依然遙遙無期,但成家的渴望始終沒有減少。正如寫實主義電影《小畢的故事》和《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劇中所描繪,失婚、原住民族的女性......同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成了老兵極有限選擇中的良伴。
多數老兵人生中最精華歲月都待在軍中,除了精進戰技外,缺乏一技之長,工作領不到優渥薪酬,社經地位不高,就算結了婚也始終在底層裡頭打轉,子女也難逃階級複製的命運。
年紀差距大、文化程度低、濃厚鄉音......都是老兵與子女疏離的原因,畢竟現實世界中,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才能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小孩可能怨他:就是因為你們,我在別人面前就抬不起頭阿。」
再者,外省軍人與台灣社會始終有一層隔閡,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沒辦法真正融入本地社會,「不是客家人,也不是閩南人、福佬人,他要如何融入台灣的社會?後來他娶的、結婚的對象,往往也不是台灣主流社會的家庭。」
台灣,
大時代無情宿命中幸運的落腳
「在家裡種田無聊,就跑出去當兵,當兵後來就稀里糊塗來台灣了。」李福鐘對外省老兵有一層特殊的情感,或許源自軍官退役的父親也來自台灣海峽的另一端。有一群人在還搞不清楚人生為何的10幾、20歲離鄉背井,俄頃間被捲入時代大浪中,由不得渺小的個人做選擇,「被放到一個宿命裡頭,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回到老家去。」
戰火漫天下的聚散離合,老兵生命歷程的起落與無奈,李教授引佛家語「宿命」一詞概括,彷彿一切皆是預定的因果命運,非人力所能更改。儘管無情,但他心中始終相信著,老兵們東渡福爾摩沙已是相對幸運的安排。
「許多沒有來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其實在1951年到1953年(共產黨)的鎮壓反革命裡頭是被槍斃的。」兩岸開放探親後,李福鐘陪同父親回湖南老家一趟,村子內的鄉親私底下提起這段陳年舊事。
當年李父和同村年輕人一起去當兵,後來國民黨的軍隊散了,他找不到回鄉的車和船,陰錯陽差之下就跟著孫立人到台灣,村子裡的那位少年則順利返家。幾年後,共產黨掀起鎮壓反革命運動,要把社會中任何一點「潛在的威脅」揪出,以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民國勢力進行清洗,「像我爸爸村子裡頭的那個年輕人就被槍斃掉」,因為他待過國民黨的部隊。
時間無情 老兵無語
70個寒暑過去,這批外省軍人逐漸凋零,既尋不回家鄉又難融入社會,成了新一代台灣人眼中「熟悉的陌生人」。瀏覽年輕人喜愛的匿名社群討論區,Dcard和PTT上對老兵誤解與歧視的文字俯拾即是,價值觀念落差成了一道弭不平的深深鴻溝。
「我們知道時間有時候是很無情,時間久了很多事情就解決,或者就消失了。」身為歷史學專家,李福鐘教授倒看得很淡。他說老兵16、17歲來到台灣,現在差不多90歲了,很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活到90歲,人生結束就結束了......不管歷史現象、社會現象,甚至社會問題,它就結束了。」
李福鐘坦言,這批老兵始終不是台灣主流社會的一員,從來沒有強大的聲音和話語權,他們不是福佬人、客家人,在部隊裡頭是低階士官兵,自然也不會是外省族群的中堅,「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非常特殊的環境,人生一直都不是那麼的光鮮亮麗。」
即便離開部隊走入社會,外省軍人大多沒有特殊專長,只能從事較低階的工作,「我並不認為這是制度上不公平,我認為這是歷史因素造成的特殊現象。」老兵意外來到台灣,蔣家父子又無力反攻大陸,他們被迫在異鄉求生,加上教育程度不高,和本省人競爭呈現弱勢的一面。
今天回望過去,這幾十萬人終將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事過境遷、物換星移,很多年輕人已不記得這塊土地上曾有過這些往事,外省老兵只存在有限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其實長期來講是命運對他(老兵)不公平,他們的人生際遇其實也蠻心酸的。」
偶然和宿命
老兵對台灣感情複雜,生活了大半輩子卻難以真正融入社會,李福鐘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省籍」。兩蔣時代每個人的身分證上都印著籍貫,似乎時時刻刻提醒著外省軍人,雙腳所踏之處只是暫時居所,不是永恆的歸宿。
「我是湖南人、我是河北的、我是山東的,每個人透過籍貫也會產生某種認同,就算你從來沒有回去過。」官方政策影響之下,加上眷村畫出一條界線,不論從心理上或現實上來看,外省軍人跟台灣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堵牆。
命運巨輪的輾壓和大時代的離合,把他們推向台灣海峽的這一端,躲過了烽火下死神的召喚,政策上的限制和禁令接踵而至。少時困在國家編織的美夢裡,中年在社會下層徘徊,老了踏上故土而至親與摯愛多已不在,公平嗎?
「我講一句公道話......我也不覺得來台灣是虧欠他們。」訪談中李福鐘多次提起偶然和宿命。從結果來看,外省軍人留在大陸命運只會更加悲慘,和國民黨有牽扯注定成為「黑五類」,就算沒被槍決,從鎮壓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近30年漫長的階級鬥爭中,只會成為政治上嚴加打擊的目標。
「我一直覺得我爸爸的case他是來對了。」1988年李福鐘陪父親回老家,聽見街坊鄰居私底下說著,「(你)去台灣去對了」,留下來肯定會是整個村子裡頭命運最淒慘的一位。更何況比起留在老家一輩子種田,台灣生活富裕程度超乎想像。
李福鐘回憶,父親家鄉村民多是世代務農,那個年代沒人家中有浴室,他們只待了2天就因熱臭實在受不了,急著回到城市裡的旅館盥洗。父親在台灣生活多年,天天洗澡早成了習慣,「台灣誰家裡沒有浴室?光是這種生活習慣,他就沒有辦法再回到從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