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餘威尚在,低溫只有14度,採訪小組按著網上資訊來到台北延平南路159號的全家超商,見到清瘦的「大餅爺爺」和他一整車手作的東北點心,蔥大餅、槓子頭和饅頭靜靜躺在那兒,品項齊全幾乎一個不缺,熱騰騰的霧氣在透明塑料袋內打滾。
幾天前,大學生社群平台Dcard上有篇文章提及「大餅爺爺在街頭賣饅頭」,盼熱心網友捧場,讓爺爺早些回家休息。不過,有位男大生不以為然,留言質疑「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年輕不長進,才淪落成這個地步」,瞬間引發論戰。
「那他為何落到今日的下場?你以後會這樣嗎?你不會吧?為何他會?」男大生無禮的文字很快遭管理員刪除,但無數的問號留在許多人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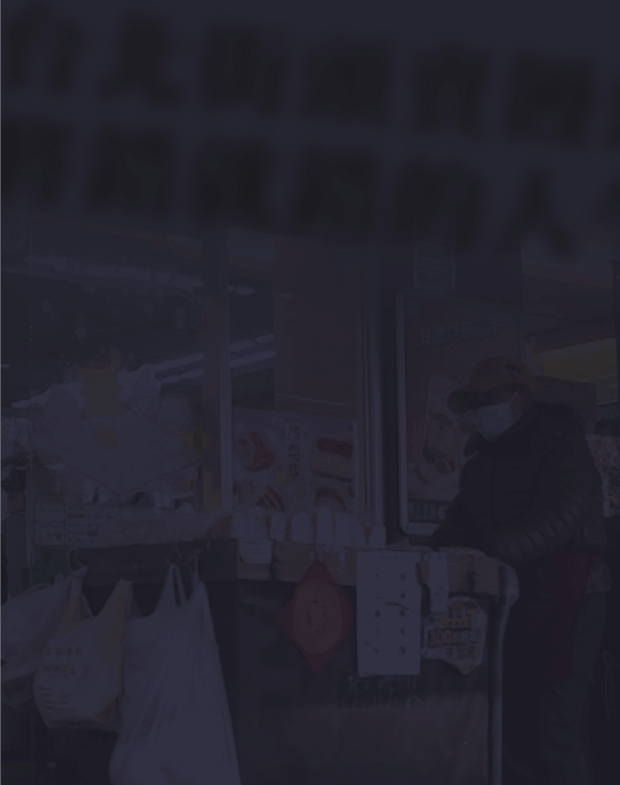
台北街頭賣饅頭
將錯就錯的人生
大餅爺爺今年93歲,是河南省開封市杞縣人,操著一口濃厚的河南腔,本名為汪相,但身分證上卻寫著「王相」。原來,國府1949年遷台時填寫錯誤,當時登記人員沒能聽清楚,他索性將錯就錯,餘生都成了另一位陌生的「王相」,如同被顛倒錯置的人生,爽朗的笑容下流露出一絲絲哀愁。
汪爺爺每天凌晨2點起床生爐、揉麵團,直到6點後才會緩緩推著攤車,一路步履蹣跚地穿越車流,來到延平南路、廣州街口,開始他一整天的工作。攤位上,琳琅滿目的槓子頭、蔥大餅、莒光餅和大饅頭都是他的得意之作,有源自東北的堅持,每樣價格卻不用20元。
見到我們拜訪,汪爺爺笑得瞇起眼,一邊熱情介紹「親手做的才好吃,我這都是真材實料,都是老麵!」儘管如此,街上熙熙攘攘,很少人為他停留,大部分時候汪相都孤伶伶地站在巷口,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即使寒風刺骨,他也只是拉了拉紅色毛帽,把手插進灰色的大夾克裡。
一位常客大姐說,伯伯喜歡與人為善,每次賣饅頭都是「半買半送」,有時少收10塊、20塊錢,常常往客人的手提袋多塞幾樣糕點,說是「交朋友」,但偶爾不走運,遇到貪小便宜的客人,這次嚐了甜頭,下次上門卻斤斤計較,硬是要求多送點東西。
大姐愈說愈氣,因為汪爺爺性子軟,凡事都喜歡和和氣氣,經不起這種咄咄逼人,每次從了,出來擺攤反倒賠本。這天,我也買了兩包饅頭回家,每顆都大得能抵上一餐,生怕客人吃不飽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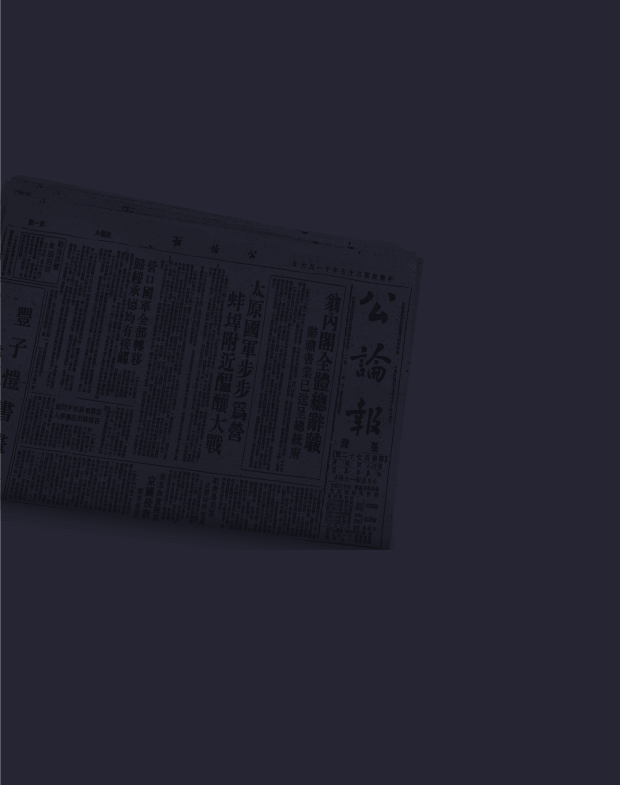
17歲被抓去當兵
那支步槍比頭高
汪相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一個大哥、姊姊,還有一個弟弟,住鄉下過著割草、趕牛的生活。17歲那一年,大哥、弟弟去了城裡,汪相晚上在家睡覺,國軍部隊闖進來抓人。和那年代無數年輕人一樣,他糊里糊塗成了戰場上的一份子,第一天發下來的那支步槍比他個頭還要高。
好在隔年日本投降,他不必經歷抗日戰場的煙硝,但他不知道,另一場足以改變他一生的戰事正悄悄逼近。
1948年冬,徐蚌會戰爆發。國共雙方投入近200萬兵力,圍繞徐州一帶展開決戰。「大廈將傾,一木難支」,風雪紛飛,國軍潰退,無數官兵走投無路,最大的包圍網有數十萬人受困,不是戰死就是餓死了。短短66天,國府損兵折將,精銳盡失,長江以北是守不住了。

當時汪相人在第55軍,屬於劉汝明的第八兵團,負責戰場南線的防禦,雖未陷入包圍,但先後執行了進攻宿縣、救援黃維第十二兵團等任務,均以失敗告終。
「機槍、大砲朝你打,交通壕裡躺了滿滿的人,有的腿斷了、手斷了,有的還活著卻不能跑了……。」汪相回憶,友軍接連被圍,一個接一個聯繫不上,那是第一次深切體會絕望和無力,只能全憑求生本能,「那時候害怕也沒辦法,撤退時只能閉著眼睛趕快跑。」

兵敗歷劫45天
逃往一座未知之島
共軍很快渡江南下。主帥劉汝明自行率第55軍、68軍從安徽撤至福建、漳州圖存實力,但共軍一路追擊,廈門戰役爆發。汪相跟戰友邊打邊跑,潰逃長達45天,晚上弟兄只能2人背靠著背,在路邊闔眼休息,如果不幸碰上下雨,那就徹夜難眠了。
「徐州打完以後就東跑西跑了,那邊(共軍)兵力比較強,打到長江以南,我們就守不住了,只能撤退,從南京到青陽,青陽再到福建,福建到漳州,漳州到廈門。」
70多年前的往事想來彷若昨日,說到一半,汪相伸手拿下鴨舌帽,指著蒼蒼白髮下一塊明顯的傷疤,「那時候我的頭受傷,被砲彈的碎片打到,只能用綁腿、衣服內的棉花包住頭,把傷口纏起來,後來逃到船上,也沒有治療,誰也沒空理你。」
兵敗如山倒,部隊在浙江沿著山路逃命,翻過險峻的馬金嶺,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總算看見一輛大運輸船停泊,軍民爭先恐後,紛紛搶著上船,不少人都被踩進水裡,莫名成了海中亡魂。
偏偏就在不遠處,解放軍的槍聲響了起來,一路是愈靠愈近,很多人還沒能擠上船,就這麼留了下來。當船隻逐漸離岸,步步脫離險境,這時汪相才總算回過神來,卻已來不及回頭向故土道別,也不敢去想岸邊那些人後來怎麼了。
運輸船橫渡黑水溝,在大浪中總是搖晃。每個人疲憊地蜷縮在一起,滿臉倦容,但連上一個機槍手沒抓穩,機槍一晃盪,險些把同袍都給掃下海裡,好在汪相躲得快,加上戰友拉了一把,才沒命喪大海。
汪相知道,這艘船開往一個名叫「台灣」的島嶼,但不知道台灣在哪,更沒聽說過這個地方。我好奇問「去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不怕嗎?」他靦腆地笑,「怕也沒用。」

第二次入伍造路
為家人做一次逃兵
1949年,第八兵團在廈門遭到毀滅性打擊,劉汝明率殘部約四、五千人倉皇逃至台灣。不過,軍隊的船剛停靠高雄港,立刻收到東南行政長官陳誠的命令,要求解除武裝。西北軍將領劉汝明不肯配合,被下令限期「徒手登陸」,否則將船擊沉。
劉汝明別無他法,這些兵員被收編、發配各軍,至此西北軍最後一支部隊瓦解,55軍番號也從國軍消失。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撤退,反而讓國民革命軍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穩住台海局勢,政府開始「汰弱留強」,非嫡系出身的軍人首當其衝,大多遭裁編勒退,在沒一技之長的狀況下,被政府組織起來去建設、開路。
汪相命運相似,來台後同樣被編散,改編入青年軍第80軍,又很快在1956年退伍,被政府安排去築路,這支1萬多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目標是打造第一條橫貫台灣東西的公路。
當時中橫開發不易,受限於工程技術和設備,往往先靠炸藥開山壁,再換人力以鑿子、十字鎬和圓鍬一路敲敲打打。汪相說,大夥白天在山上築路,晚上在路邊搭帳篷睡,舉目所及盡是懸崖峭壁,每一分秒都與死神相伴。


這些退伍軍人經受日軍侵略的炮火,見識過解放軍滿山滿谷的人海圍堵,一次次從無情的槍口下活了下來,卻一個個死在落石和炸藥下,再也沒能回家。
這樣的生活持續1年多,汪相見身邊弟兄傷亡無數、多人殉職,夜裡明月高懸,夢中鄉下青草地氣味鮮明,對故鄉和家人的思念愈發濃烈。為了再見到朝思暮想的至親,他決定做一次逃兵。
1956年,有1萬多人被動員開路,期間225人魂斷中橫公路、702人受傷,平均每公里至少1人犧牲,只為成就這條全長189.8公里的公路系統。1960年通車後,這些名字靜靜躺在長春祠的石刻上,漸漸淡出社會大眾的集體記憶。


戰爭帶走兄弟倆
他一人活著回家
「回去見家人」只是一個卑微的願望,有些人卻用了一輩子,等到驀然回首,早已錯失融入台灣社會最好的時機。如同汪相,他不會講台語,身上也沒什麼錢,連生存都成問題,靠著四處打零工,哪裡招工就去做,日子過一天是一天,一心想著回家鄉,更不可能結婚了。
1989年,兩岸剛開放探親不久,汪相如願以償,時隔40年再次踏上故土,家鄉景物變了很多,欣慰的是雙親、姊姊及弟弟依舊健在,唯獨大哥已經不在人世。他聽家人講才知道,大哥後來加入解放軍,在1950年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身份投入韓戰,沒能活著回來。
「好不容易回家鄉了,怎麼沒想過住下來?」爺爺搖了搖頭,情緒沒有太多的起伏。原來汪相曾加入國軍,有些親友態度很是看不起,加上身份上仍敏感,可能會給原鄉家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善良的他選擇默默離開,回到那個沒有家人、獨自容身的島嶼——台灣。
汪爺爺說,兩邊習慣不太一樣,他曾經心心念念,甚至是活下去的動力,但不知不覺中已習慣在台灣的生活,沒打算「回去」了,「以前會很想很想家人,現在能打電話了,就好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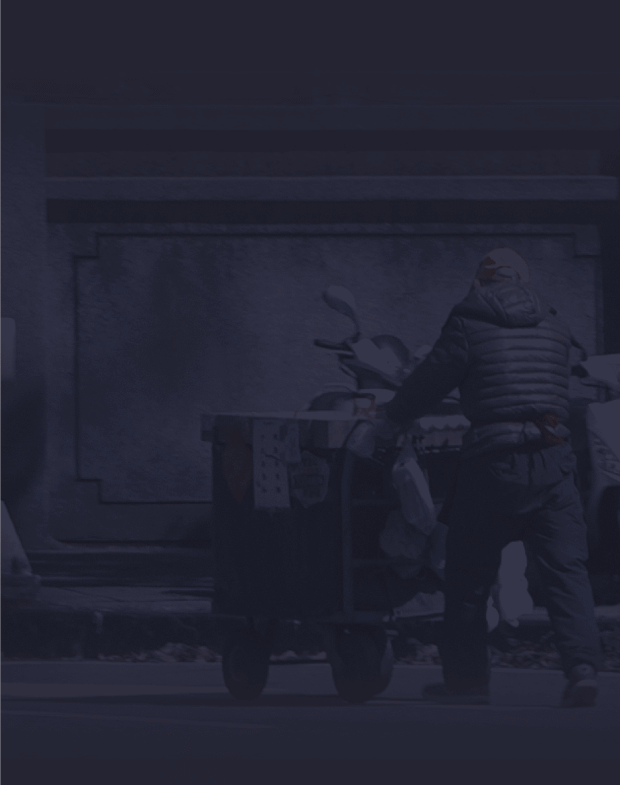
開啟賣餅人生
與鄰里結緣
附近一間川菜小館的老闆說,汪爺爺80歲開始賣饅頭,鄰里見他孤身一人,幫忙做了這輛攤車,「那時候看著他每天撿紙袋(裝饅頭)也不是辦法,伯伯真是個大好人,後來有警察來開罰單,我還拿著罰單去派出所,親自掏腰包幫他繳,也建議警方先勸導,不要對一個老人家直接開單。」
汪爺爺說,年紀大了漸漸找不到工作,便從朋友那裡學習製作東北點心的手藝,天天早起揉饅頭,擺攤貼補家用,節儉過日子,「在中華路租國宅,一個月5000多塊」。

「伯伯那你這樣賺的夠用嗎?」一位鄰里路過回答,「伯伯一個月應該是領1萬3500,從國軍裡面退下來是最低的。」另一位常客則補充,「我常常來啊,他90幾歲了,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還租房子,真的,我們政府都沒有照顧到這些人。」
汪爺爺不好意思地點點頭,沒有說得太多。我明白,他不習慣也不喜歡怨天尤人。不過,或許是爺爺賣了十幾年,附近鄰里看在眼裡,也一直默默用行動照顧著他,盡可能早些買走攤車上的「最後一顆饅頭」。
這天收攤時,我問爺爺有沒有什麼願望?他緩緩地說,住在台灣超過70年,心底早把這裡當成家,這些年賣饅頭交了許多朋友,說說笑笑一天很快就過去,現在只求社會安定,大家都開開心心有飯吃,彼此和睦共處,這就是台灣之福。
汪相一輩子所追求和珍惜的,不過是如此平凡的人生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