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外省老兵被譽為「榮民」,撕開細看卻是血淋淋的悲傷。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蕭伶伃表示,「他們承載這個社會的恨意,也承載這個社會得不理解」,只能在加害者及被害者的身分中游離失所,「榮譽在哪呢,榮譽變成可恥了」。
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榮民失去的那些人權
中華民國政府敗退來台,蔣中正為擴大總統權力,秉持「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口號,於1948年5月14日正式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有效期限為2年半,但此一法條於1991年經國民大會決議、時任總統李登輝公告後才於5月1日廢除,共施行43年之久。
蕭伶伃表示,一般內政底下維持秩序的是警察,軍人不會進入日常。軍人會在軍隊裡面,軍人所負責的應是國防事務,是捍衛國境、捍衛主權,但動員戡亂的頒布,象徵台灣當時全被納入戰爭體制,隨時處於戰爭狀態。
政府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為了讓軍人日常處於備戰狀態,完成反攻大陸的結果,「我們可以了解的白色恐怖的口述史,都有談到憲兵隊出來抓人,有的是說是警察或特務抓人,不論是特務或是憲兵隊,其實都是軍的一部分,也就是軍人」。
蕭伶伃進一步解釋,當軍人現身於日常生活中時,就是台灣進入戰爭狀態的重要證據,「即使台灣現在疫情這麼嚴重,你也不會隨便看到軍人在街上,也就是台灣目前是穩定的,我們的依歸是憲法,而不是動員戡亂條例。憲法最主要的精神不只是管理,更重要是捍衛你的人權。」
「在動員戡亂條例的限制下,人權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沒有位置、沒有角色,一切都是為了去取得政權及戰爭的勝利。所以不論是榮民或是一般台灣的人,在當時都有一個很鮮明的政治任務,就是反攻大陸,特別是榮民,他們必須要在前線。」
從這個角度去看,榮民是什麼樣的概念呢?榮民的全名是「榮譽國民」,他們捍衛政權、捍衛國家而成為榮譽國民,但他們在當時是基層,有可能成為加害者,這關乎我們如何定義「加害」。台灣最初處理轉型正義,會談到誰害了誰,但以德國來說,他們進步到不只問「誰傷害了誰」,還會追問「為什麼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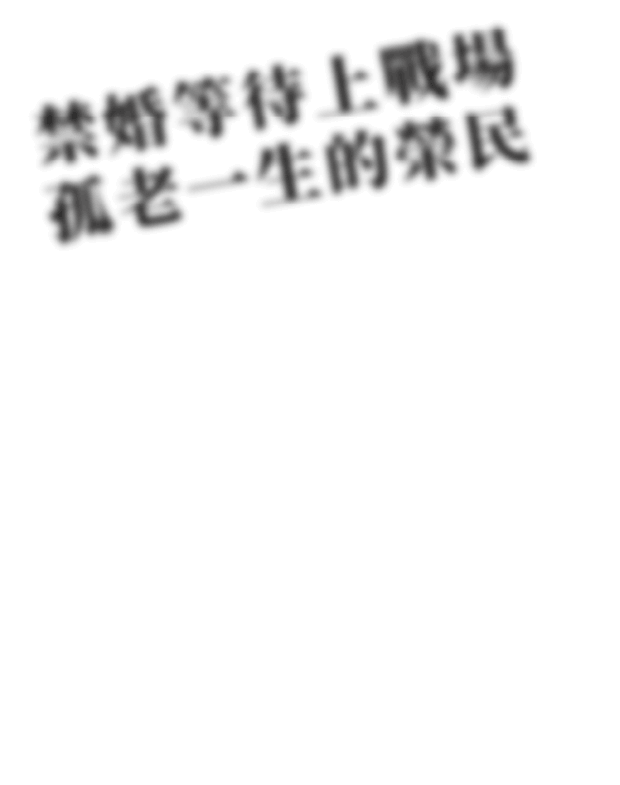
禁婚等待上戰場
孤老一生的榮民
外省老兵來台後,1952年被下禁婚令,規定提到4種人不能結婚,分別是直接參戰或擔任緊急防務職、受訓期間的學生、在軍事學校受訓後,服務未滿兩年,以及年齡未滿28歲等。
蕭伶伃說,《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後,軍人成為一種財產,而不是一個人,不具有基本尊嚴的生命,因為國家的手伸了進來,他們就失去在社會上基本上的權限與自由。
榮民的最大的不幸在於從未拿過鮮明的好處,不論財務上或是社會身分,但諷刺的是,他們被視為「榮譽國民」,榮耀卻沒有被社會主流認可,這才是社會問題。尤其是國家張力最高的白色恐怖時期,榮民以國民黨軍隊的身分在現場,實際拿過好處的卻是領導階層,並非基層老兵,但承受對外的仇恨、敵意時,他們卻是最鮮明的載體。
除了被貼上省籍標籤,榮民在色恐怖期間被捲入「敵我框架」中,以當時記錄的數據來看,超過四成以上的受害者、政治受害者都是外省人。也就是說,白色恐怖時期的「敵我框架」是人民跟人民之間作對,國家必要時也會跟你作對,你轉身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你可以是國家的人民,也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
這些底層榮民受禁婚令影響,無法發展最基本的社會關係,也就是最小的組成單元「家庭」,還得時時待命,等待國家徵召而動彈不得,這些「例外狀態」橫跨他們的青春及壯年,等到遲暮之年希望可以安穩生活、擁有家庭時,才發現有多困難,「非常多人其實是終其一生孤老的。」
蕭伶伃形容,禁婚令等於將一個人丟到真空環境中10年,除了對自我身分產生懷疑,對自我認同也會沒有憑藉點。這些單身榮民當初以娃娃兵來台,沒有專業技能及文憑,雖然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卻只能做服務業、餐飲業維生,加上受禁婚令影響,「他的不自由可能我們都沒有看到,因為單身不是選擇,單身是一種命運。」
受限於禁婚令,榮民缺少和社會有效、良善的溝通管道,長期與社會鮮少接觸的情況下被貼上標籤,直到社會自由了,早已錯過與社會對話、融入的時間點,也變老、變窮,只剩下一個人,「榮譽在哪呢,榮譽變成可恥了」。

眷村成為枷鎖
難以融入台灣社會
「不是每個人都像《一把青》一樣,能遇到美麗的愛情,在台灣有妻有女、有子弟」蕭伶伃說,榮民的問題之所以難解,就是他們的身分過度被「單一化」,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家庭,也並非每個人都是吃香喝辣的統治階級,「過度的單一化的結果就是,我們不只沒有辦法去細緻看見整個社會內部的紋理,也沒有辦法細膩去看待所謂的加害、受害關係」。
外省族群剛來到台灣時,在政府安排下住進眷村,一般都建設於軍監、軍法學校及法院等機構旁邊,「眷村就是宿舍,你為國家服務,又是軍系的一員,這個假設是軍人體系的場景,旁邊一定有宿舍。」
然而,眷村有著不同於本省其他族群的日常風情,其核心就是外省、外省軍眷的生活場域,而且內部也有階級之分,如階級高的將領可居住較大的房子。很少人注意到,上述提到被禁婚的單身榮民是不能住在眷村的,他們住的是單身宿舍,最大的歸屬是退輔會,一生都與軍人的身分脫不了關係,彷彿被烙上印記,無法逃離。
許多老兵為了有個家、融入社會,會跑到靠近山的地區自行建屋,形成奇妙的文化聚落,台北蟾蜍山就是很經典的例子。蕭伶伃表示,這些老兵與許多有著台北夢的女孩相遇、成家,徒手蓋出自己的房子,儘管是非法違建,但隨著時空更迭,現今已成為台北。不過,由於山坡的所有權屬於國產署,目前台北市政府正努力以「文化共存」的形式保存。
蕭伶伃認為,蟾蜍山象徵的不只是榮民視角下的國家暴力、戰爭狀態的問題,更可以探討移民中的合法、灰色地帶。相關單位目前持續協助老兵遷居,並讓蟾蜍山聚落成為觀光景點,希望讓年輕人理解眷村,促成跨世代的理解。
承載社會的恨意
榮譽變成可恥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外省人是不可或缺的族群。」蕭伶伃指出,當初外省人來台約120萬人,數量遠超過本省人。當時,國家發動國家政策、政治宣傳,將許多資源都集中在外省人身上,就連進入台灣大學的比例都偏高,高過本來在社會的基數比。
當時最經典的作家、最經典的電影都是由外省人領軍。蕭伶伃舉例,瓊瑤是成都人,她筆下的故事被翻拍成電影、連續劇,但主軸幾乎都是在講中國大陸故事,「她要撫慰的到底是誰?比如《情深深雨濛濛》那樣的偶像劇,竟然紅到古巨基的時代還要再重拍一次,到底她撫慰了誰,真正的本省人不會有這樣的生命經驗。」
當國家試著去形塑集體認知、集體認同,甚至是集體記憶時,不僅可以看出不公平的資源分配,以及「我們要回到中國的社會氛圍」,但在國家的監控下,本省人很少、也無法對此發問,「形成整個台灣在四年級、五年級戒嚴時期的集體認同」。
儘管如此,外省人在台灣民主化中,仍是不可或缺的族群。身為外省二代的鄭南榕便是用台語號召,推動本省化與李敖合作,知識份子們共同為了民主化、打倒威權,而努力付出。
蕭伶伃說,「這群人無形中默默推動族群融合,試圖讓裂痕減少。但問題是本土化的契機不只來自於這些政治上的要角,更重要的是本省人長期被壓抑的聲音,好不容易迸發出來,但本省人在戒嚴時期並沒有獲得同樣主流頻道,沒機會去談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認同,談論自己的政治身分,他們是被集體壓抑的」。
「有一群外省人是沒有名字的,你只會叫他榮民」,蕭伶伃表示,榮民成了國民黨軍、國民黨政府最鮮明的代言人,也因為榮民到處可見,「他們承載這個社會的恨意,也承載這個社會的不理解,他們到底得到多少好處,這裡要打一個問號,因為很多人現在處境也不是很好,也非常艱難。」
丟失生命的樣貌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和解
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8月1日的原住民日道歉和解,「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政府從現在開始,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所以第一步設立了「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蕭伶伃認為,榮民被談論時不該被扁平、單一化,而是該去談他如何進入這個境遇,這個身分為何被套到這個體上,為何貧窮、為何禁婚,貧窮又遭遇甚麼,「和解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叫做社會溝通,目的是要讓一個生命被丟失的樣貌、視角,可以慢慢的拼回來」。
「我想,這個部分會是轉型正義要去努力的」蕭伶伃說,榮民不盡然可以進入轉型正義的框架,但他們進入國家體制後,也許成為加害體系的一員,在某個加害場景現身,也可能是被害人,被定義為政治犯而清算、鬥爭。
蕭伶伃表示,無論是認識外省人,還是認識本省人,我們都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例如大家談論二二八事件的本省受害者,卻忽略了資料中有四成以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他們是「一路以來為國家賣命,為國家付出青春,為國家付出生命,為國家丟失人生的這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