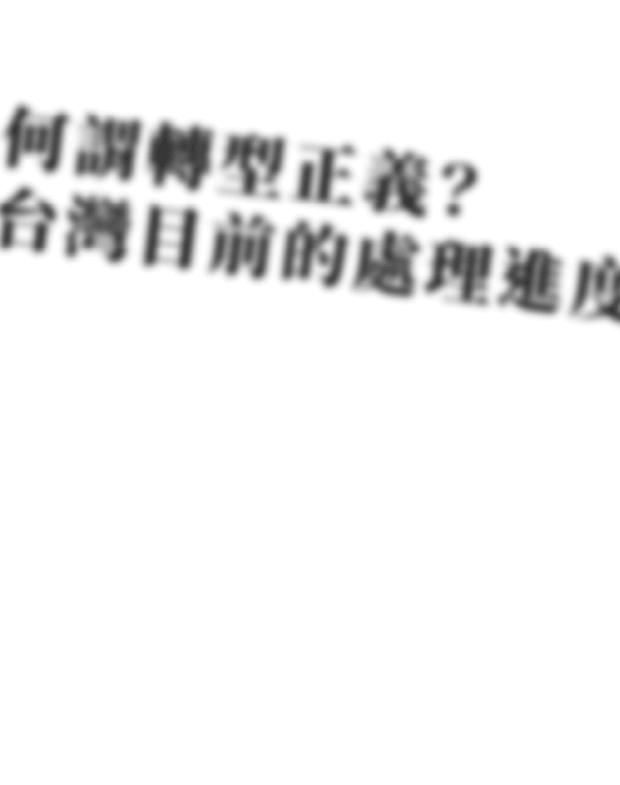
國共內戰敗退,國民黨1948年5月10日發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綁住60萬老兵,許多人終其一生無法回到故鄉,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喪命,多的是生根後定位錯亂而哭泣的靈魂。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蕭伶伃以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談老兵處境,認為台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素養需要時間。」
何謂轉型正義?
台灣目前的處理進度
蕭伶伃表示,轉型正義的英文為Transitional justice,其中justice的原意為司法,德國的語意框架為「轉型司法」,「在法的框架底下去處理過去不公不義的事情,不公不義的行為」。
不過,法不會對人格進行審判、裁決,主要是評價該行為以及帶來的後果。因此,在轉型正義的框架底下,都是針對事實進行評價,主要導向為和解的道路或是追溯、判定罪,以及確認罪的事實。
以台灣來說,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壓迫方究竟是誰?蕭伶伃說,「在過去,可能不論是4年級生、5年級生、6年級生、7年級生,甚至是太陽花世代,都會去談的問題。一定會有一個壓迫方,會有一個受迫方。」
台灣不正義的政治經驗有1945年或1949年開始等說法,有人認為是1987年解嚴之前,或是動員戡亂結束、廢止都算,定義很狹隘。但是,這些不同的定義,都是從不同角度去觀看,要如何判定台灣的不正義,以轉型正義去處理,是現在政府需要做的工作,「但我會說台灣現在看起來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總統府前踢正步的老兵
被仇恨的加害者或被害者
蕭伶伃表示,榮民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可能以不同的身分在現場,國家既得利益時,他們不見得會在,但他們仍是這體制中的一份子,「敵我關係的二元論,總是在人的認知裡面發生,我群與他群的分辨是非常重要,就是人自我認同的重要依據」。
外省族群在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占比逼近五成,他們被捲入敵我框架之中。《動員戡亂臨時條約》的敵我狀態是,人民跟人民之間會作對,「國家必要時也會跟你作對,你轉身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你可以是國家的人民,也可以成為國家的敵人,而定義這件事的,當然是國家政府。」
蕭伶伃說,「誰會在底層成為最主要的接觸介面,可能是這些榮民,可能是這些軍警,或我們所了解的特務」,外省族群的身分沒有辦法被細緻化之外,最重要是榮民的身分被捲進去,這個所謂仇視的認知框架裡。
當人民在40年的生命裡,長期被框架體制威脅一定會累積情緒,他會累積集體的悶、恨,那這個集體悶跟恨會投射到誰身上?當民主、自由、解放的年代,來的時候,當緊縮令被鬆綁的時候,這個恨跑出來的時候,誰會去承載這個恨呢?
「回想2016年的時候,一群老兵跑去總統府面前踢正步」蕭伶伃舉例,當時社群媒體上充滿許多訕笑、敵意,「我覺得這必須要被理解,在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有多麼被壓抑」,「對軍警的敵意本來就是種必然,這是一個歷史,但回過頭我們要去問的是,在裡面踢正步有沒有來自一些底層的榮民呢?」
蕭伶伃進一步推測,這些老兵中有沒有人一生未娶,或者是一生再也沒見過父親的人,「可能等到他有機會回鄉的時候家人都已經不在了,因為中國歷經戰亂,包含飢荒、文革,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平順,中國有中國的當時的困難。」
蕭伶伃認為,轉型正義中,指認每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面貌是非常漫長的工程,但這是必要的工程,「所以德國人時至今日絕對不會說我們轉型正義做完了,德國人還沒有說過這句話,德國人認為一切都還在繼續走,每一年都會花很多精神跟力氣,在特定的日子去紀念、談論發生在二次大戰,或是東西德分裂的故事」。

德國的轉型正義
從集中營逃離的贖罪者
二戰結束後,德國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才被人民看見,那是一個納粹政權集中營的加害、被害現場。雖然當時東德、西德分裂,但德國沒有停止探問的角度,反而持續追問「為什麼會有納粹?」「我們這麼驕傲的日耳曼民族,為什麼會有希特勒這樣的人?」等問題,至今都還沒有停下腳步。
「德國前兩年還在起訴活著的納粹」蕭伶伃舉例,前納粹黨衛隊(Schutzstaffel, SS)的下士奧斯卡·葛朗寧(Oskar Groening)當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負責登記、分類從囚犯那取得的動產,被稱為「奧斯威辛的會計」。
看著納粹的暴行,奧斯卡每天喝酒麻痺自己,後來才調往其他單位,卻在1945年6月10日被英軍所俘,前往英國強制勞動,直到1947年返回德國,卻將過去的一切隱藏起來,過起第二段人生。不過納粹在集中營內的暴行,讓奧斯卡每晚都看見人們走進毒氣室、丟進火葬場,受害者的尖叫聲從未停止,在他耳邊環繞,這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又稱創傷後遺症)。
蕭伶伃說,奧斯卡回到德國後每年固定捐錢給二戰相關的基金會,默默贖罪,幫助遭納粹殘害的族群,但隨著聯合國檔案開放,一名英國學者注意到奧斯卡在納粹名單中,卻沒有被轉型正義明顯評價,因此德國的評價機制開始發動,針對奧斯卡70年前的行為做出評價,而奧斯卡也很快認罪,但否認直接參與大屠殺。
「合理的轉型正義在法的框線底下,他的行為還是要被評價,只要他有個很明確的身分」蕭伶伃強調,只要這人在當時有明確的身分,就是加害體制的一份子,本來就要被法來評價,但評價後要索賠、監禁,或是公開道歉,都是可以討論的。
蕭伶伃指出,如果沒辦法對當時行為,做有效的評價,國家跟社會很難有更進一步的意願或能量往前,對國家來講是能量,對社會來講是意願。況且,透過評價才能進一步了解,這人當時為何會在那個位置,是否為自願,或是被牽扯進去,「那體制的力量有多大,可以讓社會的力量去集體反思,轉型正義最大的目標就是,避免下一次傷害發生。」
借鑒德國
台灣政府該如何進行轉型正義
「不做,就是過去這20年很慘阿!」蕭伶伃表示,藍綠對決確實拖延了探索過去的步伐,但轉型正義對台灣的關鍵是確認何謂台灣,以及台灣是怎麼走到現在這一步,進而確認台灣為甚麼是台灣等探討問題,「它是一個歷史工程,也是個社會溝通的過程」。
蕭伶伃指出,對於現在10幾歲的孩子來說,殖民問題已成為課本上讀明清時代的歷史,但記憶不過三代,以記憶學的角度來說,三代人之後都會化為塵埃。但是,有些老兵從此隱姓埋名地活者,只有少數願意談起這些過往,「老兵仍然存活著」,在記錄的這一塊仍來得及。
白色恐怖至今不論哪個世代,台灣都經歷過非常紛亂的年代。蕭伶伃認為,生命經驗的歧異之大,在那麼小的島嶼裡面,整個社會被分割成不同空間,每個人都在舔自己的傷口,走自己的生命過程,如慰安婦、台籍老兵、白色恐怖政治犯、二二八的家屬。
榮民、底層外省人、底層台灣人,或者是曾經隱姓埋名、張牙舞爪加入國民黨體制的協作地方治理的本省集團、派系,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之所以是台灣,「以我研究經驗以及個人情感來說,它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清的,或是一個定義就可以下的,多元為什麼叫多元,其實值得更進一步探究、值得去問。」
身分複雜的外省老兵、台籍日本兵及慰安婦,對於台灣歷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去多了解、多接觸,甚至鼓勵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多做一點事情,我認為唯有記憶才有辦法看到此刻的模樣,也才有辦法看到未來,那這會是轉型正義最大最大的誘因。」
老兵逐漸凋零
我們能做什麼
蕭伶伃表示,現在年輕人很喜歡在社群上面發表言論,也很喜歡談論自己。新世代與過去的世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會把鏡頭朝向自己,舊世代會習慣把鏡頭朝向對面的人。
「自我探索對於新世代來講是個重要的事」蕭伶伃說,大家可以問一問自己從何而來,從自己的家庭、朋友、社交圈出發,自我批判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開始,「那是不是非得要把每一種歧異都抓起來,才是一個合理的轉型正義?」
德國沒將所有的傷指認出來,也沒有把所有痛苦、所有因為不義政權而死去的人名全部記下來,「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盡善盡美到這種程度。」
蕭伶伃說,但還是有我們可以做的事,「如果我們已經起心動念,已經相信我們可以這麼做的時候,就可以從微觀、個人的角度開始做了,也許時間要很長,可能要再一個70年。」
她強調,我們知道沒有一個生命可以等同另外一個生命,假設用生命去看,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個群體?轉型正義的最基本要件,是要明確地指認這是一個過去的事實,而不是一個當下,必須要跳脫掉入人格評價的陷阱。
最後,蕭伶伃說,進行評價不是要去評論他是不是一個好人,或是不是一個壞人,而是要去評價他在那個時空底下,他做了哪些行為,唯有去確認行為事實,才可以去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行為,那個為什麼就是在追問體制,是怎麼把個人捲進去的,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台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素養需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