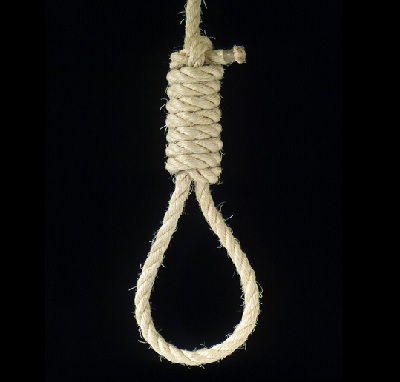品藝茶樓
有位乾隆朝的進士,為官雖說不上厥功至偉,倒也博了個廉潔自守的清名。到了嘉慶年間,老進士經歷這數十年的宦海沉浮,終也感到厭倦,加上自己唯一的兒子李璋無心仕途,便向朝廷告老還鄉,舉家搬回河南定居。
李璋在城裡的大街上覓了間舖子,學做茶葉買賣。仗著遠近官員和當地仕紳對老進士的景仰,生意日漸興隆,索性另外找了個地方開起茶樓,還聘了兩三名夥計幫忙張羅,茶樓裡每天總是熱熱鬧鬧的。
可惜好景不長,某天夜裡的一場大火,把茶樓燒得只剩焦黑的殘柱斷樑;更詭異的是,李璋的妻子李許氏和一名叫做張五的茶樓夥計,竟在同一天消失的無影無蹤!沒幾日,街頭巷尾便流傳起李家媳婦和夥計私奔的耳語,當這閒話傳到老進士耳裡,竟讓他老人家氣的中風身亡。
這天晚上,李璋在後堂用過齋飯,剛進靈堂便見到李許氏跪在老進士的棺槨旁痛哭。李璋怒火中燒,上前一把揪起李許氏怒斥道:
「賤人,妳還有臉回來?若不是妳和那張五私奔,還一把火燒了品藝樓,爹他老人家哪能這麼早歸天?如今又來作態哭棺,是何居心?不過妳回來的正好,一起跟我見官去!走!」
李許氏抬頭望著丈夫,她雙眉緊蹙,涕淚交流的模樣,卻也似真情流露,並非裝腔作態。她扶著公公的棺槨站了起來,言道:
「相公為何要這般冤枉妾身?」
「妳還敢喊冤?爹說那天申時許,妳拋下他和女兒不顧;我到處問人,都說妳往茶樓去了。莫不是去見那姦夫,共謀私通?」李璋仍不相信李許氏的清白,更不待李許氏辯駁,便一巴掌往她臉上搧去!只是李璋這一搧,卻似揮在那香案上,打散了一縷輕煙。李璋一時摸不著頭緒,回過神來才發現李許氏憑空消失了,只留下李璋兩手上濕滑油膩的噁心觸感與腥臭的餿水味道…
十六年後,李璋的女兒李純出落的亭亭玉立,更是鄰里間口耳相傳的美人胚子;奈何李純她娘李許氏淫名在外,遲遲無人願意上門提親。
這天,李純拎著一籃繡品出門,要去繡莊裡交貨。半路上聽聞一名醉漢在街上鬧事,便夾雜在人群裡看熱鬧,不想這醉漢瞧見李純長的年輕美麗,一時起了色心,上前推開人群想調戲李純!然而這醉漢走近李純定睛一看,竟嚇的臉色發青,全身顫抖還尿濕了褲子,往後跌坐在地上,連滾帶爬的倉皇逃離。圍觀眾人不知緣由,只聽得有人喃喃自語的說著:
「孫大個兒今天是怎麼了?平常沒神沒鬼的,怎麼今天像撞了邪似的?」只是李純顧不得理會他人嚼舌頭,便離開往繡莊去了。
當晚,李純作了個夢,夢見一隻孔雀又走又跳的進了一間茶樓,還往櫃檯旁的小門裡去,穿過伙房來到後院,不停的用鳥喙敲啄著牆角的大水缸。夢醒後,李純百思不得其解,但見窗外天色微亮,便換了衣裳,到前堂給爺爺燒香。
李純給祖先燒香本是她每日清晨必做的事情,今日卻不知為何,看著老進士的畫像看得出了神,也沒察覺李璋走進前堂。
「在看什麼呢?」
「女兒給爹爹請安了。」李純對李璋行了禮,又回頭看著畫像,問道:
「爹,女兒常聽您說起,爺爺當年是朝廷裡的三品大員。」
「當年妳爺爺是朝廷的大理寺卿,為官正直清廉,因年老體衰,倦於理事才告老還鄉的。有什麼問題嗎?」李璋自己也給父親燒了炷香,然後在一旁坐下,繼續聽李純說著。
「女兒在想,爺爺身上的補服,繡的是孔雀沒錯吧?」
「是啊。」
「昨晚上,女兒夢見了一隻孔雀…」李純把夢中所見,鉅細靡遺的交代著,只見李璋皺著眉頭,一語不發的暗自思量;當年李純尚在襁褓之中,並不曾抱出家門,更休談是否到過茶樓,卻為何能對茶樓的格局景象瞭如指掌?難免心存芥蒂。
「爹問妳,可曾在夢中見著那茶樓的招牌?」
李純仔細回想,確實在櫃台上方懸著一塊牌匾。
「有,櫃台上的牌匾,似乎寫著"品藝"二字。」品藝兩個字從李純的嘴裡說了出來,讓李璋震驚不已!更兼有孔雀入夢,莫非是李純的爺爺回來託夢?若如此,又為何不肯於夢中直言相告?李璋著實不解,只是他見女兒尋思難解,便以江湖術士的解夢說詞,草草交代了事。
當晚,打更的剛報過子時,李璋卻還在書房裡看書。他聽著梆子聲漸行漸遠,打算將家裡巡視一番才回房休息,卻在女兒房門前,聽見李純不斷發出痛苦的低鳴聲,聽起來就像她想大聲叫喚,卻讓人摀住嘴巴一般。李璋心頭一震,顧不得禮俗,一腳踹開房門,只見李純身體蜷縮在床上,兩手緊抓著被褥不放,李璋只得趕緊將她搖醒!李純一睜開眼見到父親,淚水就像潰堤般滑落,嚎啕大哭了起來。
「爹…我又夢見了…我又夢見了…那孔雀敲啄的大水缸裡有…有屍體…是我…是我的屍體在水缸裡呀!爹…」女兒的夢境太過詭異,李璋一時之間也不知該作何解釋,只能好言安慰女兒莫要惶怖,但其實連李璋自己也感到恐懼不安。
第二天正午,李璋決定把事情弄個明白,便帶著李純來到當年遭付祝融的茶樓廢墟一探究竟;那裡雖然雜草叢生,卻仍可從殘柱斷樑上看出當時的規模。李璋領著女兒來到後院,卻尋不著夢中的那只大水缸。
「說起來,我也不記得自己在那場大火之後,看過什麼水缸,我一度以為茶樓裡所有的東西都被燒光了。但是,若果真如妳夢中所見,肯定事有奚翹…」李璋正說間,忽然聽得背後土牆崩塌,一道身影飛也似的逃離該處,疑似窺探李璋父女多時了。
李璋望著那人的背影,只覺得好像在哪兒見過,李純卻認出那人正是數日前在街上鬧事的醉漢孫大個兒。
「妳說誰?孫大個兒?他是以前在這茶樓掌杓的廚子呀!不過茶樓失火之後,也沒來討要工錢,聽說是離開城裡到外地了。」
「爹,女兒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到繡莊裡交貨,半道上見他醉醺醺的,還到處惹麻煩,那時我就聽見有人喊他叫孫大個兒。不過…剛才看他慌慌張張的模樣,說不定是知道些什麼,我們不妨找他問個清楚。」
李璋想了想,對方畢竟也算是個熟人,即便一時間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就當是敘敘舊也不錯,便和李純兩個人沿途尋訪孫大個兒的蹤跡;不久就打聽到,孫大個兒回到城裡已有數月,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幫人幹點粗活,賺到幾個錢便跑去喝的酩酊大醉,天黑了就到城隍廟旁打地鋪,活像個乞丐似的。
「看看這天色,你們想找他的話,可以到城隍廟口等他。」街上的小販提供了線索。
李璋父女倆來到城隍廟前,果然見到孫大個兒坐在廟門邊,神情緊張的盯著每一個從他面前經過的路人。然而當他見到李純時,又像那天在街上一樣恐懼和顫抖,一起身便往廟裡奔逃,不慎撞上剛要離開的香客。
孫大個兒倒坐在地上,眼見李純一步步朝自己走來,竟害怕的兩腿發軟無法起身,雙手不停的在自己面前揮舞;一個體格壯碩的大漢,卻像個三歲孩子般哭喊,要李純別再靠近自己。
眼前的情況著實詭異,卻在李璋要上前攙扶孫大個兒時,聽見李純以嚴厲的口吻質問起孫大個兒。
「我總算逮著你了!說,當年你為什麼要殺我?說!」
李璋聽見這話,雖說確實是從李純的嘴裡說出來的,但這口氣並不是平常的李純,甚至連聲音也不像,卻又感覺這聲音有些孰悉。
李純轉頭看著李璋,眼神卻變得溫柔許多。
「相公。」
「妳?妳叫我相公?妳是…」
「我是李許氏,純兒的娘呀。」這話讓李璋難以置信地瞪大了雙眼,但這聲音在他的記憶裡,確實是李許氏沒錯。只是李璋還來不及搭上話,便聽見孫大個兒語無倫次的對李純叫喊著:
「不可能!妳已經死了,為什麼還要回來糾纏?妳可別怪我,是妳逼我的!當初我確實趁著茶樓裡沒有別人就侵犯了妳,但我起初並不想殺妳,是妳堅持要報官,才逼得我不得不痛下殺手!是妳逼我的!是妳…」孫大個兒一時慌亂,竟自行將這無人知曉的過去和盤托出。
附身在女兒身上的李許氏更進一步質問。
「那張五呢?張五也得罪你了嗎?」
「張五?呵!算他倒楣,我把妳的屍首塞進餿水缸裡,他正巧採買回來見著了!我知道他那張嘴肯定守不住,沒等他反應便一刀結果了他。正好,讓妳在黃泉路上有個伴,我也算是對得住妳了!哈…妳們都不知道,我還費了多大的一番功夫,才讓茶樓給燒個精光啊!」
李璋在一旁聽的怒不可遏,掄起雙拳便要往孫大個兒身上招呼,卻突然聽見驚堂木響和著一聲喝斥!
「住手!」
眾人如從夢覺,赫然發現自己身處衙門大堂,孫大個兒那一番莫名的自白讓自己全招了供,知縣著人給他在供狀上畫押,收監候斬。
李璋和女兒回到茶樓廢墟,果然在後院的土牆邊挖出那只餿水大缸,可憐的李許氏和張五早已化作兩堆白骨。
「難怪…難怪…」李璋回頭看著李純,果真像極了他曾經刻意遺忘的愛妻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