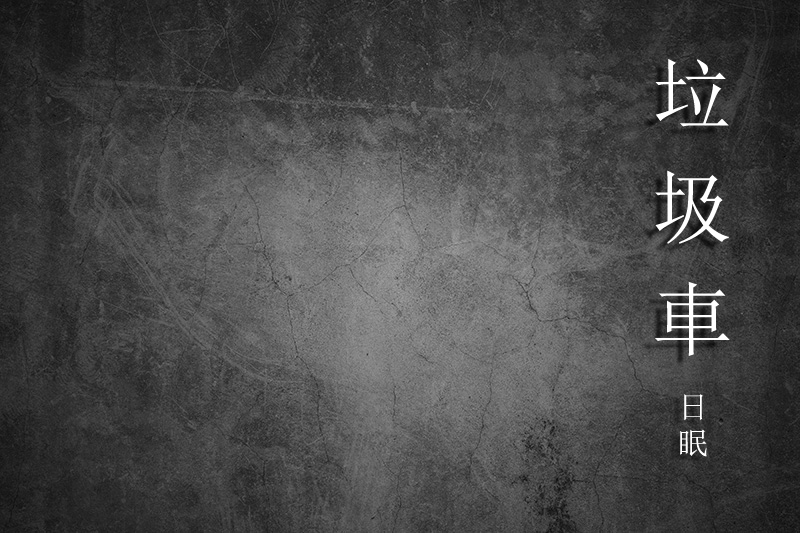不了情。下集
前一集請看這裡:
https://events.ettoday.net/activity/ghost2018/article/21292隔天去上班的時候,公司物流部的帥哥主管問我,
「Alice,你是半夜去pub釣凱子了嗎?黑眼圈像紫色眼影啊有三層耶!」
「唉,說來話長。」我跟這個帥到沒人性的同事一直是好哥們,而且他很特別,年輕的時候曾經殺過人──他私下偷偷說的,就是未成年所以當時沒有坐牢,從此改過自新,所以我都喊他「牯嶺街」(源自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牯嶺街聽完我的話,表情嚴肅地跟我說,
「我跟你說過吧,我皈依的師父是OO山的高僧,」
「嗯,記得。」其實我早就忘了,因為我很討厭被傳教,宗教一直是我又敬又怕的東西,大概前未婚夫沉迷道教導致我們退婚分手的影響,多年來我始終對宗教敬謝不敏,雖然因為家裡的關係我還是會禮佛誦經的。
「我師父早年寫過一本地府遊記,我覺得你是去了那裡,因為你描述的風景、感覺,就跟我師父當年親身經歷過的一樣…」
我很感謝牯嶺街沒有潑我冷水,說我喝酒作夢、胡說八道,雖然他說的我也沒有很相信。
那幾年,牯嶺街一直說我有佛緣,要領我進師門,可是我都沒有答應──因為,我總覺得自己不應該屬於任何一個宗教團體。小時候我是每星期上教堂的(因為教會可以打發時間還有點心吃啊),但是,我始終對於宗教,沒有很深刻的感受。
小時候我可以聽見上帝說話──但我認為那是我們自己心裡的聲音,一如我可以輕易讀懂佛經,可是,我對其中的世界的理解,跟出家的姑姑不同──佛教的天地,那是我們抬頭可見、卻終其一生都到不了的遙遠異世界,這是我的理解,人唯有透過自己提升精神領域,才能脫離肉體的限制,在九九八十一次的輪迴之後,到達另一個境界。
至於是往上提升、還是往下沉淪?那就看你自己決定,沒有誰會幫你。
所以,我不求神不拜鬼,與其求無形的,為什麼不自己努力?我一直這樣想,直到前幾年,我萬年單身之後──把Chan的相片收起來以後好多好多年。結束了台灣的工作,我帶著簡單的行李,拋下了過去的一切、遠渡重洋來了日本。
說真的,雖然後幾年不再碰佛經,不再禮佛,可是、家父過世的之後,我確實在家中見到了他老人家,我相信人的靈識會以某種形式,有如一段記憶存在於我們周圍;直到家父對年,靈位併入祖宗牌位,移到寺廟裡之後,就連家母都甚少夢見父親了。
沒有牽掛了,於是我拎著簡單行李到了日本──對,我把Chan的一切都留在了台灣。
在日本,還是有若干奇妙的經歷──日本是個神道國家,有八百萬眾神,真的是走到哪都有神明──神社多得跟甚麼似的,雖然我不打算拜異國神,但也不得不懷著敬畏之心,在人家地頭上,確實不該撒野啊。
我居住的小鎮在大阪郊外,有個德川幕府初期興建的觀音寺,每年五月都有盛大的祭典,整個大阪地區的人都會跑來。有一次我突然想,自己的小鎮有這麼有名的地方,怎麼都沒去過呢,於是忙完課業之後就穿著涼鞋出門去。
乖乖我的天,日本的寺廟真的很喜歡建在山上啊,望著那一條沒有盡頭似的長階梯差點腿軟,剛下過雨、天空灰灰的,正好是傍晚時間,腦中閃過,
「啊,我怎麼在逢魔時刻來這裡…」
然後就被蚊子咬了,還腫了三個禮拜,真是不該亂說話。
那天我拍了很多相片,包括那條長長的、被濃豔綠色蓋住的,感覺很像時光隧道的階梯。然後,前輩就敲我line了,
「學妹,你那張相片,樓梯那張,我看了很不蘇湖。」
「暗怎?」
「有天狗,好多,好多。」
前輩日文非常好,從事媒體工作,多年來還是跟我私交不錯,有陰陽眼的他,偶爾會跟我說一些鬼話,我也不知道真假。因為家庭因素他每年要來日本很多次,幾十年來已經累積七十多次,也在日本「看過」不少。
他說他見到的天狗只有頭,在相片裡飛來飛去朝著鏡頭猛撲,讓他感覺很不舒服,不過我啥也看不到啊,就說了我是麻瓜。之後我又去了好幾個神社,都是當作參觀風景,沒有很尊敬的心態;但是,那之後我大病了一場,非常慘。
就是,整個人嚴重過敏,嚴重到無法走路,房東幫我送醫之後,又吃了很多苦頭,花了好幾萬日幣的醫藥費。最後,我已經受不了那個痛苦了,去醫院之前對著天空說,
「我認輸了,以後會入境隨俗,雖然信仰不同,還是會尊敬日本的神明們,請原諒以前我白目。」
說完之後,那天幫我看病的是該醫院的部長,居然會講英文,而且對我非常親切,隔天我的病就好了大半,根本不用住院,之前一個禮拜受的苦,好像一場惡夢一樣,從此,我對日本的神明非常尊重…。
在人家的地頭上,還是不要太鐵齒為好。
然後,在日本發生了另一件事──我相信,也會是這個故事的ending──我跟Chan的故事的結尾。
「Hi,where are you from?」語言學校開學那天,我隔壁坐了一個眉清目秀的東方男孩子,濃眉大眼、臉色有點蒼白,穿著時髦得體,而且舉手投足就是一種微妙的氣質,好像出身良好那種大少爺一樣,因為他都跟同學說非常純正斯文的英文,所以我也用英文跟他搭話。
「Hong Kong。」他英文非常好,我以為他是不會說中文的那種英籍香港人,結果猜對了一半,他是英籍香港人沒錯,但是──會說中文,平白跟他烙了好幾天英文,才發現這個同學雖然在英國長大的,母語是英文,但也會廣東話,普通話甚至完全沒有港腔,還會流利的韓文,只有日文不好,所以才來上語言學校。
香港同學有個很少見的姓,是一部很有名的宮鬥劇裡面的滿清大姓。
「挖,你跟甄嬛有沒有親戚關係啊,那樣你中文名字叫甚麼?」
「我叫Chan,不過,你還是喊我英文名就好,」他說了一個N開頭的英文名字,
「我們家一向都用英文名的,Alice。」他慢騰騰地說,從那天開始他都直接喊我Alice,沒有因為年齡差別而當我是長輩。
他一直沒有跟我說他幾歲,同學都猜他跟我一樣30幾(偷笑,其實我已經是個大媽了,只是沒有結婚生子、外表保持得還不錯,班上韓國同學全部以為我只有35歲上下)。
在京都學插花的他,每天來往京阪之間,放學有一段路跟我搭同樣的地下鐵,於是每天都找我陪他散步去車站,久而久之、我們也會一起吃飯,甚至一起喝酒。我漸漸知道,他跟我一樣喜歡紫色,跟我一樣喜歡同個冷僻的線上遊戲,喜歡吃的食物口味很像,就連眼睛的顏色都跟我一樣,是淺咖啡色的。
我把我們的相片放在臉書上,一堆人說我們長得好像,只有前輩嘴賤,
「你們根本是母子吧?」
我偷偷笑了一下,
「我才生不出這麼大隻又這麼帥的兒子。」
N的英文非常好,就是道地的英國腔,學插花單純是興趣,偶爾做點翻譯或寫作的差事,其實並不缺錢,因為祖上是滿清貴族啊,家裡根本不需要他工作。他覺得自己日文不好,
「Alice你有空教教我啊。」他很喜歡纏著我問各種問題,其實他會那麼多種語言我才羨慕呢,我也只有日文稍微可以在他面前賣弄。
「Alice你懂得好多喔,我要一輩子跟你做好朋友。」他不只一次這樣對我說。
「少年仔,不要隨便跟女生說甚麼一輩子啦,信口開河不是好習慣喔。」
「不管,我要一輩子纏著你!」他難得露出像小孩子的表情,而我,真的有好像多了一個兒子的感覺。
漸漸我們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始終不知道他幾歲。
「我喜歡老的東西,老電影、老作品,我第一部電影是第凡內早餐,最喜歡義大利導演ooo的xxx…」天啊那電影比我還要老,
「別喜歡老女人就好,哈哈哈。」我忍不住笑了。
這個年輕人,有著超越實際年齡的靈魂,溫柔斯文到有點像gay,去了夜店都被同志搭訕;問他又說他只是喜歡所有漂亮的人,性別年齡根本不重要,喜歡最重要。
我想也是,現在的孩子,想甚麼根本不是我那個世代可以想像的,我就像欣賞一部新小說那樣,靜靜地觀察著他。不知道為什麼,他有好多地方,都跟Chan一樣…
我勸他搬來大阪,不到一星期他就繳了違約金退了京都的房子,搬到大阪來了,可是我們還是離得遠,因為我住在郊外。
「我喜歡夜店,可以的話每天都想去…哪,Alice你也搬來大阪市內啦,這樣我們可以每天去喝酒,不醉不歸…」
「免了,」翻了個白眼,我是來日本唸書、重新開始另一個人生的,又不是來當酒鬼的,所以我才住在鄉下小鎮啊。
他搬來大阪之前,帶我在京都逛了一次。
「你到底幾歲啊?」我們在先斗町走著,然後繞到了鴨川旁。
「年齡又不重要,就像名字只是代號啊。」
「幾歲啦?」
「下個月生日過完我就25了。」
「Alice你好襯紫色,我也好愛紫色。」他看著我的手提包,把手機從口袋拿出來,說要跟我合照作紀念,
「我們喜歡的東西都一樣耶!」身高一米八幾的他,俯身貼近我,
「看鏡頭喔,」
他不知道,我是因為Chan才喜歡紫色的,而我心裡,會一直一直都有Chan的位置。
他是1993年出生的,就在Chan昏迷變成植物人之後那個月,他在香港的家,離Chan生前住的地方不到一公里,就在港島半山。
「Chan,所以,我們真的又見面了?」我心裡想,然後腦子浮起那天在bus stop前面,Chan嘴唇微張好像對我說了甚麼,而我一直沒有聽清楚。
我看著i phone鏡頭面帶微笑,跟這個年輕的Chan在鴨川旁邊留下了合照。
「走吧、讓我再陪你走一段路吧。」他把皮夾跟手機硬塞進我的小手提包要我幫拿,好像跟我認識已經很久很久那樣。
「好。」我點點頭。
就算只是巧合也好,我想我心裡,會一直都有Chan的位置的,一直一直。
我們終於,又見到面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