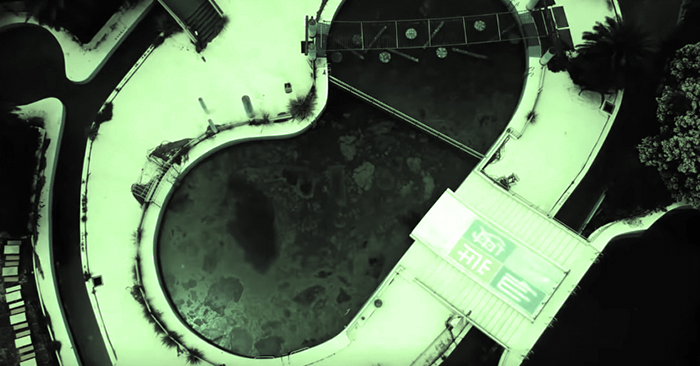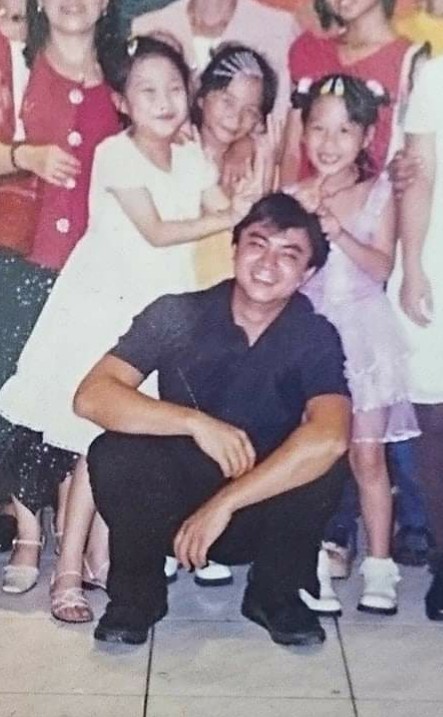暗房的故事
黑白相片要印得好,很不容易。一般印刷油墨很難呈現那種純粹的黑,一種極致的黑。印得出那種黑,才能對比出無瑕疵的白,還有他們之間,那存在著無限多階調的灰色。
因此,攝影師堅持以傳統沖印的方式完成拍攝的相片,一種幾乎已被淘汰的手工業。顯影、停影、定影,再用水沖洗,大約五、六分鐘的時間,就只是專心等待一張相片的誕生,一個過去的影像重新在眼前搬演浮現。
沖洗相片的暗房時常只留一盞包著紅紙的燈泡亮著,暗紅的光線從下往上打向牆面,在狹窄的空間裡來回反射,在身後形成多個影子。時常,視線沉浸在迷濛的光線久了,轉頭時會不知道哪個影子才是自己的。
每位攝影師都應該要有件無與倫比的作品和相應的那段故事,故事是這樣的:
我讀大學的時候,數位相機雖然已經風行一陣子,但社團的學生們,仍著迷於手沖相片的美好,又或是耽溺在自己塑造的文青感中。總之,學校暗房的使用時段總是被排得滿滿的,老師優先、再來是趕畢業的學長姐、可愛的學妹,最後才是我們這些沒地位的學弟們,即使想提前預約通常也要等上兩週的時間。借用表上密密麻麻的簽名,一直要到放學後的時段,紙上空白的部分才漸漸顯露出來,時間愈晚,紙張愈白。遠遠看那張表,從黑到白,呈現出一道堪稱完美的灰階漸層。
學校位於市郊,第八節下課後,特別安排專車將學生送回市區。因此,傍晚六點過後還留在校園裡的,除了少數自己有車代步的學生之外,只剩下像我這樣,為了特定原因而逗留的人。我喜歡挑選深夜無人的時段借用暗房,從機台上透鏡的投影,仔細對焦、曝光與測試,沖洗拍了整整一個月的相片。校園的角落、友人的笑容、女孩的背影,還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微小物件,他們會從底片相反的黑與白,按照曝光時間的長短,重新浮現出正確的灰階色調,那是他們當時所接收到的光的比例。
我一開始會跟在學長後面借用到八、九點,再央求學長載我回到市區。自己有了車之後,愈來愈習慣在晚上十點之後使用暗房,一直待到午夜,甚至更晚,一直到暗房裡昏紅的燈光彷彿都要溶化了視網膜,才帶著略為渙散的腦袋與精神,悠悠離開校園。於是,每個月選定一天的深夜沖洗相片,逐漸成為我生活的儀式,持續到我畢業的前一天,仍如往常到校園沖洗自己最後一個月的學生時光。
那天,我照例在暗房裡攤開一捲捲的底片,就著微弱的紅光,想像那些底片最後呈現的樣子。對焦兩分鐘、曝光十三秒、顯影一分半、定影兩次共三分鐘,記不得真實的時間流到了哪裡,只知道那時除了撥動藥劑與水時發出的輕微聲音之外,周圍安靜到似乎連自己呼吸的聲響,都異常清晰。
「咚!咚!咚!」門外突然響起急促而厚重的敲門聲。暗房為了不讓多餘的光線透入,因此門板相對厚實,沉重的敲擊聲打破了原本空氣的靜謐。由於以往不曾有人在這個時間點前來打擾,我猶疑了一會才向外答話,請他等一等,手上的相片才剛放進顯影劑中,不能讓光線照進來。一分鐘、一分半、兩分鐘,門外安靜了下來,但我無法專心,每個步驟好像都快了幾秒,不由得更加焦躁。
「咚!咚!咚!」急促而厚重的敲門聲再次響起。我嘴裡碎念咒罵著,一面趕忙把相片夾到晾乾處,一面轉頭回應。暗房的門板雖然厚,但由於些微的光線並不影響沖洗作業,因此門底下還是留有一條縫隙。依稀記得當下我轉頭朝門口望去時,門底透進來的光線不自然地閃了一下。長時間專注在一項工作後,要讓思緒與身體轉移到另一件事物上不是很容易,我在濃濁的暗紅光源中起身,好像花了比預期久的時間才來到門邊。
「誰呀?」我提高音量朝門外喊了聲,但並沒有獲得回應。用力推開門,門外是深沉的午夜,與兩個鐘頭前的模樣沒甚麼區別。往外多走幾步,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並沒有看到其他人影。我惱著怒氣無處發洩,但也只能回暗房把剩下的相片洗一洗。轉身往回走,門口的白熾燈從上往下照著,在牆面及地面複製出兩不同灰色階調的影子。有那麼一剎那,我覺得那影子好像不是我的,由深到淺,由黑到白,影子也有它自己的漸層。
我再次檢視最後那張來不及處理的相片,稍微晾乾了的相片紙上,是這間暗房建築外觀的相片。我想不起來這張相片是甚麼時候拍的,但最後的成像黑白色塊分明、明暗對比強烈,從純粹的黑到無瑕疵的白,過渡了無數多細緻的灰階色調。特別的是,相片裡暗房的那扇門上,怎麼看都好像有隻敲門的手,從裡頭向外敲打著。那門那麼厚實,恐怕要相當用力,才能從外面看出來吧。而我卻捕捉到了那一刻,我想,或許這是我拍過最好的一張相片吧。
故事說完了,那張相片就是攝影師無與倫比的作品,只不過,那張相片不是他拍的,是我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