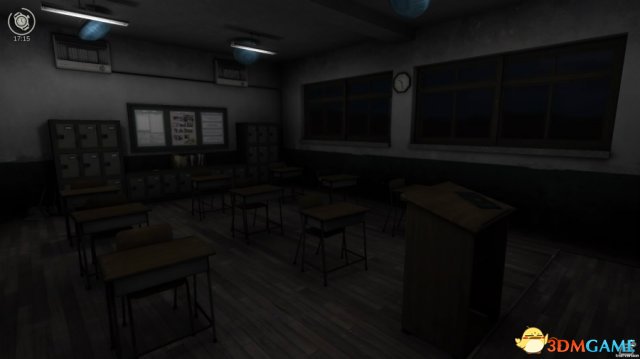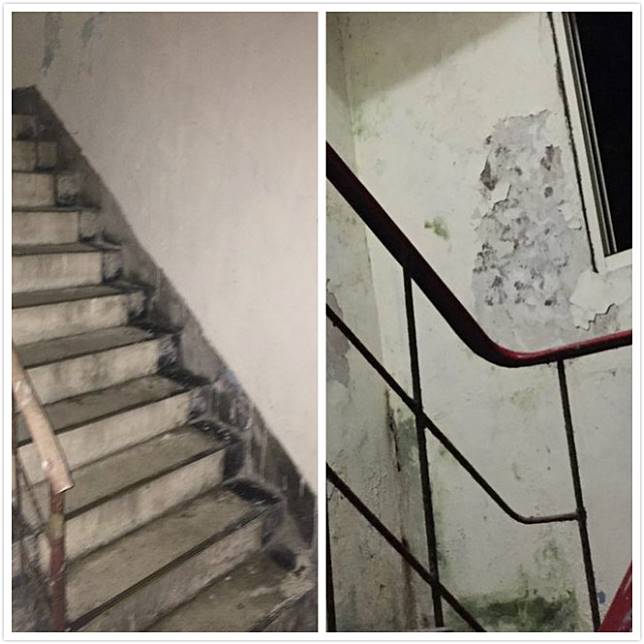廟裡的姓名(2017大家來說鬼-民間魔神仔冠軍作品)
負責舉辦迎新的朋友突然出了車禍,逼不得已只好找我頂替。雖然不情願,但看在他拍胸脯保證,迎新過程當中看到喜歡的學妹,他一定會幫忙牽線,我也只好悻悻然的答應。
原本把這當作苦差事,想說消極的應付即可的我,沒想到在迎新的那天,真的遇到了一個極對胃口的學妹。
他跟我一樣離開家鄉來讀大學,畢業於家鄉頂尖的女子中學,外表看起來應該是個愛讀書的乖乖牌。出乎意料的,當我跟她聊過幾次天後才發現,她平時的休閒活動是登山與騎車。
「我也很常騎到××溼地看海呢。」我說。她眨眨眼,說:「那你知道燈塔再過去……」
她開始向我推薦景點,而且話匣子一開,還難以關上。這正巧合了我的意,於是我以方便交換景點為由,要到了她的LINE。
一轉眼,三個月過去了。
我們兩個的關係也從單純的聊興趣,變成更進一步的聊生活了。
我想這就是曖昧吧,總會在人生增添許多美好的、繽紛的光彩。
「對了,學長。」某天,她突然傳了訊息來,「你想不想去爬××山?」她問。
「妳是說妳家附近的那個登山步道?」我問道。她家離山比較近,沿著大路走可以經過不少適合老年人的步道。
過了幾分鐘,她才傳了一張笑臉的貼圖來,並附上一句:「要嗎?」
我知道這就是「那個時刻」了,決定我們兩個的關係會更加親近,還是永遠只能維持現況。
現在我的回答必須表現的既不積極,也不遲鈍;又不能太快回答,也不能讓她等到沒耐心。
我想了大概10分鐘,然後用簡短的字句搞砸了這一切:「嗯。」
到了當天,她似乎沒有把我的笨拙放在心上,還是十分期待這次的健行。
「好吧,我們出發吧!」她站在我面前大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想過,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著她笑的如此開心。
我聽從她的意見,選擇了一條人比較少的路線。一路走來,除了幾個帶著遮陽帽的大叔與大嬸外,不見其他路線常有的攤販與餐車。山中蟲、鳥、獸競相爭鳴,卻不會感覺到喧鬧,反而相當的寧靜。
認識她的這幾個月,我跟著她一起去過不少地方,為了早日能追逐上她的步伐,不只將身體加強了,連心靈也因為常沐浴在自然中,也變得開闊了起來。
「山的寧靜,讓我們聽清楚了內心的聲音。」我希望她不要吐嘈我臨時想到的句子,但她似乎被別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絲毫沒有吐嘈的意願。
「奇怪了。」她說。
「怎麼了嗎?」我站到她身旁。
「這條步道應該只有一條路啊,怎麼會在這邊岔開?」我疑惑的看向她比的方向,再看看路中間的告示排,左邊寫著:
420M觀景台。
右邊則寫著:
200M。
「應該是臨時開的新路線吧。」我說。
「那為什麼沒有寫是什麼地方呢?只寫了距離沒寫地點,很奇怪吧。」她歪了歪頭。
「那,妳要不要走看看?搞不好我們會是第一個到達的喔。」我說,「就像哥倫布一樣。」
「不要吧,我覺得怪怪的。」她難得的露出了抗拒的表情,我卻沒有意識到,還繼續說著不負責任的話:「沒關係啦,只有兩百公尺,來回還不到這邊的路程呢!」
接著,再我的半強迫半請求下,她還是跟著我走上了那條不明的道路。
這條路應該是尚未修建完成,兩旁的樹遮蔽了天空。即便時間非常接近正午了,氣溫依舊非常的沁涼,我也暗自竊喜自己不至於滿頭大汗。
「學長,」她突然停下腳步,「我們回頭好不好。」
我轉過頭看著她,發現她的臉有點泛白,可能是中暑了,但是這邊這麼涼,怎麼會中暑?
「妳還好嗎?」我問,趕緊扶住她。
「我覺得這邊真的不太對勁,我從剛剛就有點耳鳴,不管怎樣,我們回頭吧。」她說。
「可是,我們應該快——」話未說完,忽然感覺身後有一股視線。
我趕緊回過頭,是一名帶著斗笠的和尚,不,他們有四人。
似乎刻意隱藏了臉龐,斗笠壓得低低的,看不清面貌。四人沙黃色的袈裟在陰暗的小徑更險明顯。
四和尚即便看見了學妹滿臉病容,也裝作沒見到似的,往我們的方向慢慢走了過來。
當下的我渾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眼睛死盯著這四個人,深怕他們會做出什麼奇怪的行為。
當他們走過我們身旁時,我跟學妹都明顯感覺到了一股寒意,我內心是更怕了,學妹也不禁發抖了起來。
一直到他們經過我們,走了一段距離後,我正準備再繼續關心學妹時,走在最後面的和尚突然停下了腳步,並緩緩的回過頭,
當我與他對上眼的瞬間,我的身體立刻做出了反應,抓起學妹的手,頭也不回的往反方向奔去。
我看見了。
我看見它的臉了。
那是人類的臉沒錯,但那個笑容,那個笑容,那個笑容實在太詭異了。絕對不是正常人做的出來的表情,更不用說是和尚該有的表情。
簡直像一個非人之物在模仿人類似的,表情實在太猙獰、太噁心了。
我抓著學妹的手狂奔,終於跑到了路線的終點,是一個木製的涼亭。
學妹似乎沒見著那人的臉,但也被我突如其然的反應嚇到了。
即使早就見不到那群人了,即使跑到了涼亭,也只是兀自喘著氣,不發一語。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開口:「回去吧。」
她看著我,相當識相的點了點頭。但沒想到我們才正準備踏出涼亭,雨滴就落在額頭上了。
滂渤大雨阻礙了我們回去的可能。這雨下的又急又強,出了3公尺就幾乎看不見路了。
「幹,這到底是什麼狀況。」我顧不得在學妹面前的形象了,走到涼亭的另一端罵了起來,沒想到更讓我震驚的,涼亭這頭可以看見另一條步道,此時那條步道竟是大晴天,行人熱的不斷用手搧風。
當下我就知道我自己究竟陷入了多麼危急的情況,情急之下,竟對著另一條路線的人大吼大叫,希望能引起注意。
但正如我原先預想的,他們似乎完全沒有察覺這裡正發生的事,不論是滂渤大雨,還是在大雨中吼叫的人,都像隔著一道牆似的。
學妹似乎受不了了,終於崩潰的大哭了起來,跌坐在地上,將頭埋到腿中,唸唸有詞:「我就知道我不該來。」或「我知道錯了。」之類意義不明的話,我也只能先放棄求救,在她身邊安慰她。
當下我只想結束這件事回家好好睡覺,跟學妹的關係也早就不重要了。
但這件事似乎不想結束,我突然聽見了「咔啦、咔啦」的摩擦聲,然後身子就突然傾斜了起來,不知道過了幾毫秒我才突然意識到,我們所處的木亭正在下陷,隨時都有可能跌落山谷。我趕緊抓緊學妹的手,要跑出涼亭,她卻像是生了根似的,即便我出了相當大的力氣,她依舊不動如山。
「轟」一聲巨響,我的記憶突然中止了。
再恢復意識時,雨已經停了,亭子也已經崩塌了,所幸亭子掉在一個平台上,離原本的地點不過2、3公尺,即便背著學妹我也有自信爬上去。說到學妹,她人呢?我趕緊起身尋找她,卻發現自己的右腹部被一根木棒貫穿,當自己意識到痛時,整個人趴在地上拼命哀號。
「學、」一個微弱的聲音從耳邊穿來,「學長?」是學妹!
「我、我、我受傷了啊。」我可能是邊叫邊說。「我也是,」學妹沿著亭子的殘骸爬了過來,我看見她的腳也插著許多小木片,突然感到一陣難受,便忍耐住了叫聲。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兩個確認沒事,才慢慢的爬上原本的平台。
此時山霧開始壟罩,也見不到另一條路了。
木棒插的似乎也止住血,短時間沒什麼狀況,走回原路應該綽綽有餘。學妹的狀況就不太好了,她的左腳似乎傷了韌帶或神經,沒辦法好好走路。
「我扶著妳吧。」我說,讓她搭在我的肩上,此時的我一點也不因為接觸而感到開心。
說也奇怪,本來200公尺的路,不知道走了多久也沒再見到岔路。正當我不耐煩的想開口詢問時,終於見到了岔路,旁邊還有一座小廟。
「那邊,是不是有人?」學妹問道,她的臉色十分蒼白。
「好像真的是……」我看著那個模糊的人影,不敢直接靠近。
那個人卻似乎發現了我們,走了出來: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翁。
「你們還好嗎?」他問,我不想吐嘈他的視力有多差,眼前這兩個人怎麼看都不像還好。
「我們受傷了,可以請你幫我們求救嗎?」我說。
老翁沒有開口,只是隔著小廟的柱子指了指另一條岔路,這讓我一股火上來了。
「你就不能代替我們去求救嗎?」我用盡力氣吼了老翁,然後就開始喘氣。
他則是舉起手中的掃把,好像在說他有多麼重大的工作要做似的,然後就開始掃起地,無視我們。
「別管他吧。」學妹在我耳邊輕聲說,我看向她,臉色似乎更難看了,眼睛半闔半張,似乎要睡著了。
「我趕快送妳下山,妳不要睡著了。」我說,瞪了老翁一眼,就往他說的方向走去。
走著走著,覺得腳步越來越沈重,卻感覺不到腹部的疼痛,瞬間只想要坐著休息。學妹的呻吟讓我回過了神,她似乎快撐不住了,我得趕緊加把勁才行。
又不知道走了多遠,身邊的景色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陽光似乎完全沒有移動,我甚至沒辦法分辨時間了,學妹突然一個踉蹌,倒在路邊,我趕緊靠過去扶她,卻發現她的胸口起伏逐漸微弱……
「宗興……,」他叫了我的名字,「幫我跟我的父母道歉。」她說完就閉上了眼。
我來不及叫她別說這種話,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我不知道是憤怒,還是悲傷驅使著我再度走回小廟。
如果當時那老翁願意幫忙求救,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我們都會得救。我一直想著這一切。
「你!」當我看到那老翁時,不顧傷口的血滲出衣服,揪住他的衣領,「你這個王八蛋!」
但我實在太虛弱了,連手都握不緊了。
我跌坐在地上,自暴自棄的問著:「到底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老翁又指了指那條路,我不敢相信他竟如此冷血,我的視線跟著他指的方向,穿過牆面看著那條路。
突然我靈機一動,才意識到他並不是在給我們指路,而是指著牆面上的照片。
我這才意識到這是一間祭拜山難死者的陰廟,而他指的照片,上面正是我與學妹的照片。
下面寫著「梁宗興 2017/07/××」和「黃沛真 2017/07/××」。
我突然感到一陣暈眩,乾嘔了起來,世界開始旋轉,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