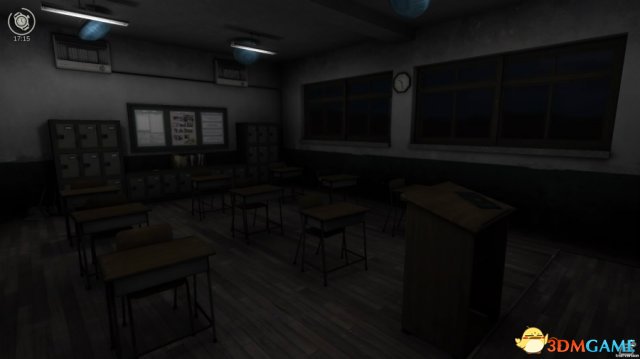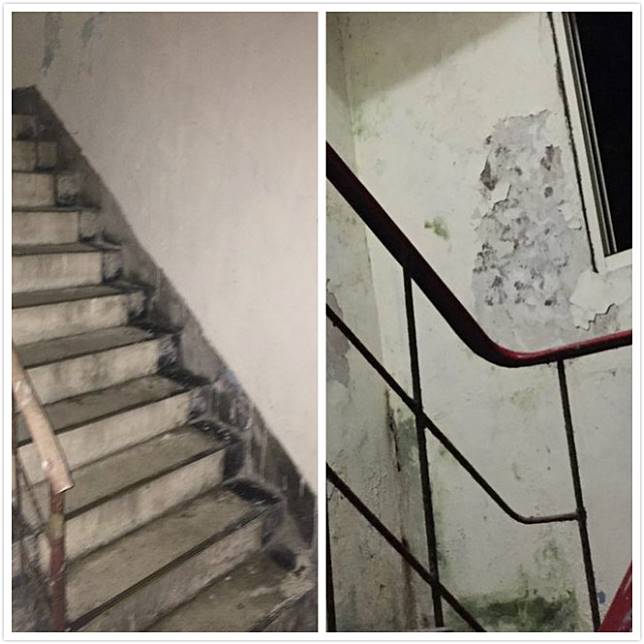手
那一年頻頻出國公幹,隻身一人在毒梟橫行的國家採訪。住宿條件不錯,入住的公寓式酒店,套房是studio式的,一進門左邊是小廚房連著吧臺、還有小客廳、雙人床、只要把活動屏障拉開,就能隔開設備和床了。
第一天認生,加上之前在同個國家的小鎮的某一酒店被“鬧”到深夜換房,因此認定第一晚是關鍵,睡得好不好,有沒有“東西”,第一晚後就能知曉。因此,第一晚充滿未知,夾帶恐懼,就連洗澡也會害怕的那種,雖然我完全沒有在洗澡時被“偷襲”的經歷,但洗澡彷彿也是人於清醒中最脆弱的時刻。
由於這裏海拔高,氣溫相對低,我把自己裹在棉被裏,躺在床的右邊,開著燈,看著電視等著自己毫無預警地入眠。其實,光與聲能給予安全感,卻也很難讓我睡得安穩。這時,床邊的電話響了,收線有些不好。“阿女啊!阿女。”親切又熟悉的聲音。是阿嫲,我對著話筒大叫:“阿嫲!阿嫲! 收線不好,根本沒法溝通,這樣就斷了。
醒來。原來是夢。畢竟阿嫲已去世5年了。想來是爸爸今早掃墓,告知我身在危險國度,要阿嫲保佑我,阿嫲大概是擔心吧!心裏有一絲暖,恐懼少了些許。沒多久,迷迷糊糊中又進入睡眠狀態,期待再接到來電,以慰思念。
這時,電話聲響倒沒有,身邊竟然多了一隻手,我下意識地抓著它,沒有溫度,卻也不冰冷,還來不及感到恐懼時,那隻手動了起來,反抓著我,手上的指甲一根接著一根觸及我的手腕,又尖又長,緩緩地就插入肉裏。痛。
醒來。是驚醒的。手已不在,心跳不止,即使我可以,但我不敢張開雙眼,一動也不動,念著佛經。天曉得,我也只會一句阿彌陀佛。我也忘了自己怎麽度過這個漫漫長夜。只知道天亮時,隨身帶著槍的接待人入房來,我也把筆記、工作、電腦全堆滿在床的另一邊,畢竟我習慣了單人床,無法翻來覆去。或許是接待人的煞氣,或許是沒有“空間”了,那隻手沒再出現。我忍著住了10天,每晚依舊戰戰兢兢,心裏卻總是默念地說,只是暫時借住,沒有占據的意思,雖然我非常清楚,那個擁有長指甲的它一直都在某個角落盯著我。這個房間,I’m not a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