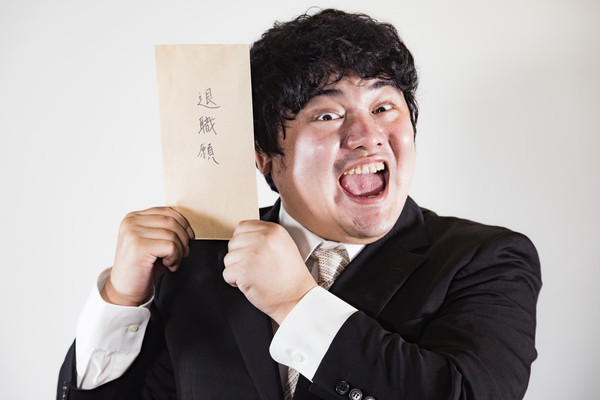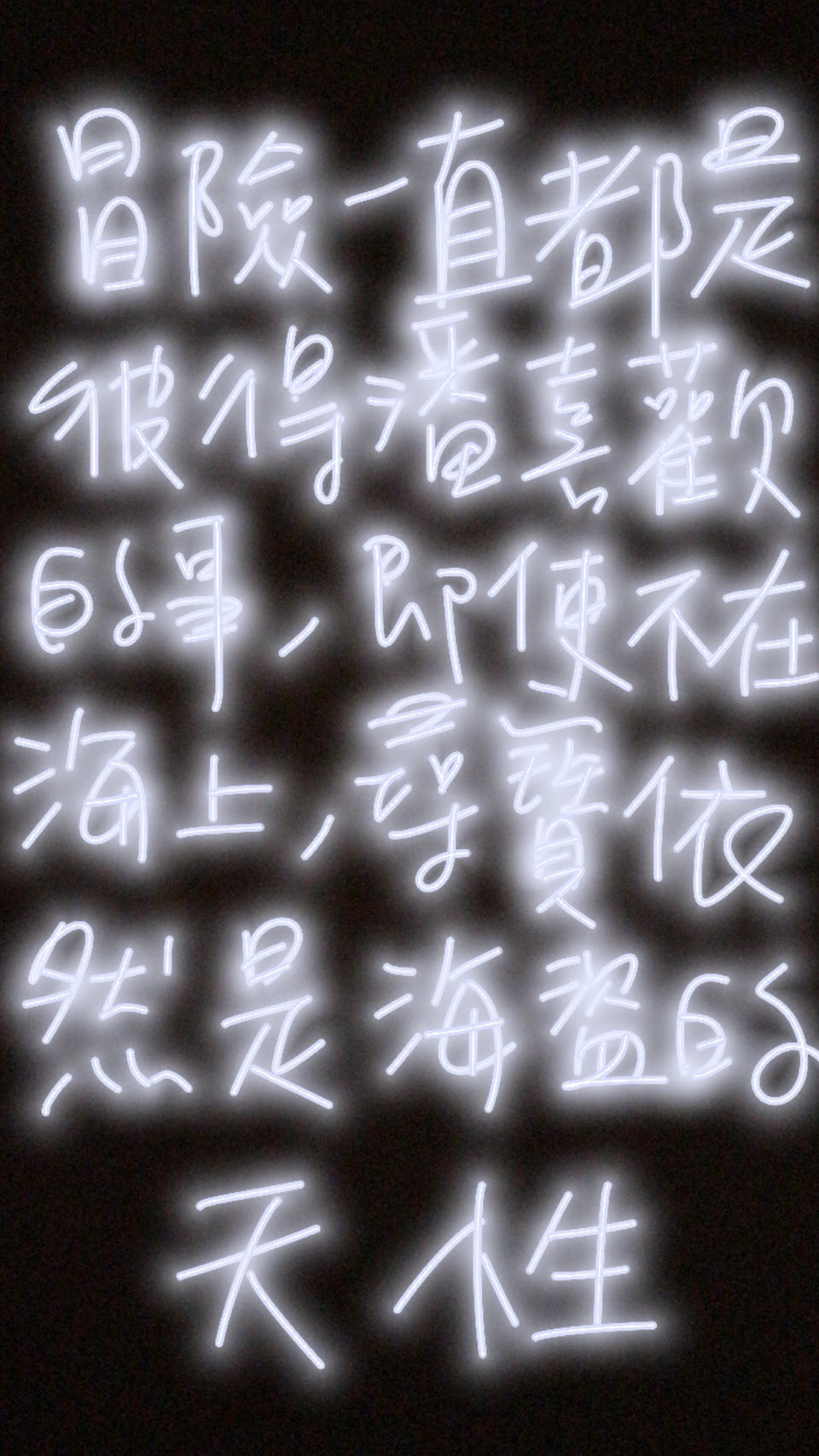#人命計算式
人命計算式
「金錢是被鑄造出來的自由。」我忘了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屠格涅夫說的名言。辦公室牆上時鐘顯示11點整。腦袋早已昏昏沉沉,肚子也咕嚕咕嚕抗議著宵夜在哪兒?實際上,我連晚餐也還沒吃。
17樓外夜景一點都不吸引人,18樓的時尚大牌員工及白領階級老外早已逍遙在不夜城之中。
腦中閃過不好的念頭,交往兩年的女友,說不定此刻正摟著其他男人;我卻抱著下午四點才拿到的厚厚卷宗,拚命與事證、法律意見書及最可惡的老闆奮戰至今。
毋須翻閱卷宗或法條,我早已明瞭女友已對我失去了當初的愛;之所以不肯離去,只是因為「習慣」。
愛情上的習慣比冤獄判決更可怕,非常上訴或再審有機會翻案,可是,掉入習慣的陷阱中時,雙方當事人卻沒有一方勇於提出上訴,畢竟…不存在「爭議」呀!只是一種眷戀與不捨,甚至是不甘心。
各方面的習慣就是一種成本概念:忙碌疲憊的工作讓我不想耗費時間成本認識新的可能對象,認識之後,又得花費心思進一步瞭解對方,也必須讓對方理解我,再進一步,則雙方都必須再度付出更多的成本來磨合、調整彼此步伐,甚至是性愛的默契。好多好多的成本!倒不如窩在習慣裡頭,至少還有一絲絲溫暖及溫存。
習慣,真是昂貴的毒品。
之前聽聞某前輩與結褵15年的太太離婚。
若加上戀愛,總共是20年相處時光,竟然在女兒讀國中時「分手」,令人感到詫異。投入的成本能如此毫不在乎地捨棄?愛情,真的可以計算成本?
我越想越糊塗。如果不能計算,那麼我在害怕著什麼?
因週末將至,必須在美國時間週五結束前,把中英文法律意見書送呈給潛在的大客戶:一家美國知名的保險公司。
腦中浮現此刻在夜店、Lounge Bar裡頭把酒言歡的紅男綠女,啜飲著我最愛的Pina Collada,讓微醺氛圍包覆著疲累身軀,或許…有意想不到的邂逅在醞釀。
老闆的催促來電,讓我在幻想中醒來,灌下苦澀咖啡後,決心要在午夜前離開充滿銅臭味的辦公室。這圈子出了名的「女魔頭」老闆在外頭拉生意,不時打電話回來督軍。煩悶情緒蜉蝣在複雜的卷宗之間,冷冰冰的電腦螢幕注視著我的空洞與孤寂。
去年跨年夜時,我在工作中度過。雖透過位處精華地段事務所的窗子可清楚看見台北101燦爛煙火,但心中只有煙花散去後的落寞。
這一行早就沒了以往的繁榮光景,十年前懵懂抉擇,註定走上了不歸路。低薪律師滿街跑,搞業務行銷的更是不在少數。
很多人竟然轉職當法院書記官或檢察事務官,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荒謬。
更離譜的是:實習律師開始不支薪了!甚且有知名事務所打趣說:「看來可以考慮向實習律師收費了。」
漂鳥般無助的白袍小巫師們(註),懷抱著希望卻無從施展任何魔法,便屈服在體制下,甚且還沒能賺錢就必須繳納各個區域的公會會費─簡直像繳納保護費一般。
律師們素質參差不齊,更導致收費及收入的紊亂。但坐在權力頂端的老闆們,依舊年繳上千萬的稅金。小律師們只能苦哈哈地硬撐,期待自己爬上那個位置。
良莠不齊的法學素養,也是促使我今日工作超過12小時的原因。
原本是某知名事務所接洽的美國大客戶,但該事務所卻無法精確處理台灣法律與英文間的銜接,因此尋求老闆合作及協助,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出具一個案子的中英文民刑法之法律意見暨風險報告書。同一時間,國內最大的事務所也同步進行這項作業,雙方比的是速度與風險評估的精準度,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容忍極限內,幫助美國方面的高層在台灣法治下「全身而退」。
某位婦人在知名運動健身中心的三溫暖室中摔倒,腦部受創,送醫時仍舊清醒,但經過手術後卻陷入昏迷,甚至因腦出血而有生命危險。
我的任務就是:阻斷「因果關係」,簡單來說,就是說明婦人的昏迷與健身中心「可能」的過失無關─然而法律的規定卻是不論有無過失,健身中心都必須要負上責任。我必須把一切過失責任都推給「醫療疏失」以及婦人本身的「與有過失」。
退萬步而論,倘若真要負責時,可能付出的代價是多少?
也就是:我正在計算著一條人命值多少錢?
愛情無法計算成本;一條寶貴的人命卻可以?
而且必須盡可能地「壓低成本」,才能接受委任。
本件利潤不高,老闆著眼的是後續的利益。一旦受到青睞,之後將有源源不絕的訴訟或非訟案件主動送進來。為此,2個小時前,老闆憤怒地摔了我的意見書。並非內容寫得不好,事實上,中英文的分析與遊走法律極限的「卸責」抗辯寫得相當好,全然地把所謂的「道德良知」與「法感情」捨棄在金錢大門之外,考慮的就只有客戶的利益與成本風險。
然而,我估算的「人命價額」係三千多萬元,老闆氣憤地罵道:「你知道競爭對手給出的金額是多少嗎?只有一千萬出頭!必須壓低在這個價額之內,我們才能贏。」
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撿起了被丟在地上的意見書草稿,重新檢視卷宗有無漏掉的事證線索尚未運用在「人命價額計算式」之內?
寒冷的11月底,卷宗的冰冷毫不留情地堆疊在桌上,我赫然發現:今天正是那位陷入昏迷婦人的丈夫生日!
頓時,我感覺喪失了「身體的自主權」:一個人孤伶伶地飄盪在全然黑暗的世界中,茫然無所依從,無法言語甚至無法表達任何情感,什麼都見不到,黑暗之中聽見遠方天際傳來規律的鼓聲,然而那聲響與震動卻越來越微弱。
我好害怕!不停地流淚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就連眼淚也背棄了我的意識。空虛感如黑洞般強力吸蝕,我的身形一點一點地消散,好想擁抱著「什麼人」,藉由體溫傳達自己的情感。
無奈地,自己的體溫早已不存;剩餘的只有無止境的「空」。
電話鈴聲冷不防響起,我從一片虛無中伸出左手拾起話筒:「死了,對方剛剛過世了。動作也未免太慢了。」老闆說完後逕自掛斷電話。
780萬元。我正好重新計算完該位婦人的生命價值。
而她卻在丈夫的生日當晚辭世了,遺留下來的是780萬的和解上限金額。
我的淚水,在當下也遺留在冰冷的卷宗內,成為看不見的「被告事證」。
午夜天空飄下了寒冷的十一月之雨,我拎著無比沉重的公事包,裡頭裝有週六早晨緊急會議的人命價值資料。
雨水呵護著沒有撐傘的我,髮絲逐漸黏在一起,冰冷的感覺穿透過西裝、襯衫直達胸口。
午夜的雨中,我想找個人擁抱,輕輕地在他耳邊低語:「我過去及未來剩餘的人生,究竟價值多少呢?」但是,那個人並不存在。
全身濕透的我,轉身走進夜店,讓Pina Collada的液體緩慢流遍喪失自我的身軀。
註:台灣律師袍為白領白襟,檢察官則是紫色,法官袍係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