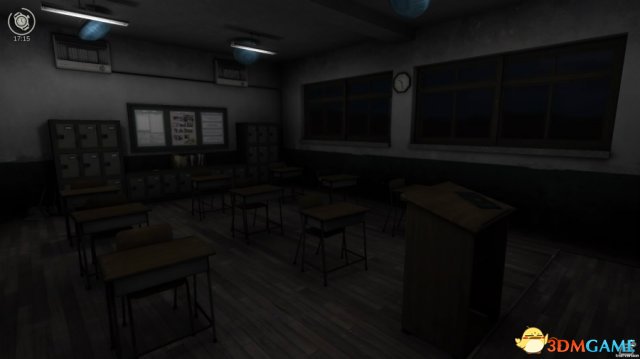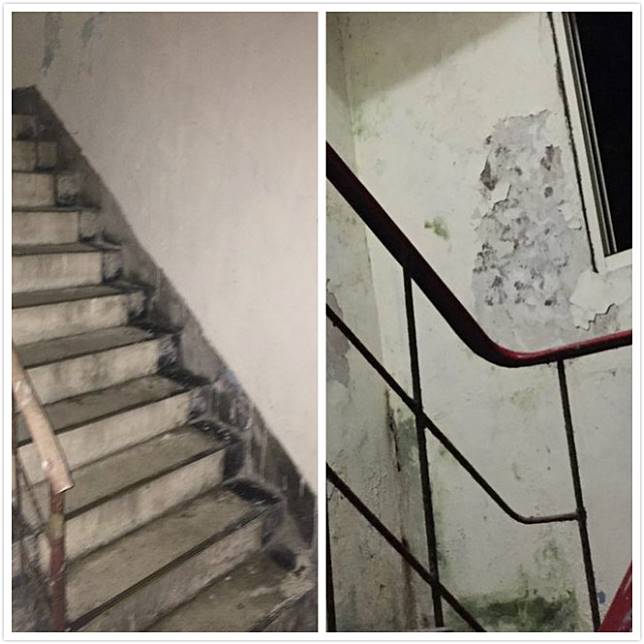母湯卵共
阿公過世了,在一個寒流隆冬的夜晚,因為慢性病住院開刀的併發症,他來不及過農曆年,就先到天上去看佛祖了。媽媽在電話那頭哭得好傷心,泣不成聲的她只叫我趕快回家幫忙。就這樣我連夜兼車南下,回到老家門口撲通一跪大喊一聲「阿公!」,七七四十九天的告別法會於焉展開。
其實我對阿公的印象自從我離家北上工作以後就一直是模模糊糊的,我只記得小時候他很喜歡買糖果給我和弟弟吃、帶我們去參加廟會活動最喜歡跟進香團到處去遊覽。等到長大以後每次回去就只會看到看護的外勞推著輪椅上的他在院子曬太陽,而阿公只是嘴巴半開的在打瞌睡。他的離開其實對我來說並沒有感覺到太真實的悲傷,我夾在至親過世應該悲痛萬分的社會期待裡和好像只是隔壁老爺爺過世的尷尬裡暫時搬回老家幫忙。
阿公不是什麼仕紳名流,但因為他這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小鎮,所以幾乎認識住在這裡所有的人,白天來弔唁的鄰居朋友如過江之鯽,爸爸和阿伯忙著向客人致謝、聊往事還有和法師葬儀社確認流程,媽媽和伯母在廚房忙進忙出張羅所有人吃喝和善後,我和弟弟就是在旁邊摺蓮花、抄經文確認香有沒有續……所有大小雜事都一手包辦。一場喪禮都還沒開始,家裡已經累得人仰馬翻。
疲勞的累積讓我對這一切漸漸有點感到厭煩,有幾個守靈的夜晚我會偷偷掀開用來圍住保存阿公屍體冰櫃的黃色布幕,看著躺在發出嗡嗡響的冰箱內那個曾經在陽光底下睡覺的阿公,現在也不知道是因為在冰櫃冰太久還是死了以後會肌肉萎縮所以阿公在裡面也是半開著嘴巴像在睡覺,而正對著嘴巴的玻璃好像起了一層吐出的霧氣……那不真實的感覺再度湧上心頭,然後因為害怕我會快速退出布幕外面,回到位子繼續折著折不完的蓮花花瓣,希望喪禮可以早點結束。
那天爸爸神秘兮兮地和法師不知道在討論什麼,只聽那個帶著冠帽的紅衣人用台語說晚上要做法……什麼又什麼的,然後拿給我和弟弟一人一疊符紙說要按照他畫的路線一家一家去送符,並且通知收到符的鄰居們今天晚上有法事請將符貼在門口並且避免外出。我一看那地圖就覺得頭頂發昏,法事的地點是在距離這裡有大概三公里外的空地上,把符挨家挨戶送過去還要說明用法,這一趟回來我應該也累死了……正要開口抗議時,只看見爸爸對我使了眼色,然後說了句:
「囡仔人有耳無喙!」
我跟弟弟只能摸著鼻子掛著兩個熊貓眼出門了。
中午出門等到符送完回到家都已經是傍晚時分了,媽媽只叫我和弟弟簡單的用個餐休息一下,晚上一家人又為了那個神祕的法事忙碌起來了,成箱成堆的金紙元寶被裝上了車,法師們也開始對著祭壇喃喃的誦經,我撐著快要闔起來的眼皮,站在旁邊聽著怎麼也聽不懂的經文感覺精神和肉體的疲憊都已經到達了極點……
就這樣熬到了深夜,在恍惚之間,媽媽突然拍了我一下說:
「出門了。」
拖著沉重的腳步,我跟在媽媽的背後準備往空地出發。那天晚上氣象局發了低溫特報,室外的氣溫只有八度,幾乎是一走出去我就想回家鑽進溫暖的被窩內。在蕭瑟的寒風中前進,耳邊不時會傳來走在前方法師的搖鈴聲和低低的誦經聲,在漆黑的道路上一行人緩緩的移動,我好像也聽到前面有人在哭的聲音……
到達目的地以後,只見那塊空無人煙的空地中間用一幅很長的鐵絲網圍出了一個圓,早先在家裡成堆的金紙元寶幾十箱都放在鐵絲網旁了。法師誦經的聲音停止了,他要我們各自去箱內拿金紙和元寶圍著鐵絲網的圓繞一圈。
「媽,這到底在幹嘛?」我終於忍不住問了。
媽媽壓低了聲音說:
「阿公明天要出門了,我們要燒一些金紙給路上的無主孤魂,請他們讓阿公一路好走啦。」
我瞄了一眼放在旁邊都快有一個成人高的紙箱堆,嘆了一口氣說:
「鬼賺錢都比我容易。」
媽媽聽了白了我一眼,還罵了一句:
「囡仔人黑白講話!」
可能因為冬天風大的關係,燃燒的金紙一碰到強風立刻轉為烈焰,沖天的火光照的四周明晃晃的,連八度的低溫都被蒸發得無影無蹤。風變得更強了,突然間我好像看到了什麼東西往火裡面衝進去了,咦?一個、兩個、三個……好多的黑影竄出,它們動作迅速的衝進火裡……。還來不及發出聲音問站在旁邊的弟弟有沒有看到,我就發現那是一群不完整的「人體」:缺手斷腿的、鼻塌眼凹的、捧著頭顱的、腦殼脫落半掛在臉旁邊晃啊晃的……全部都擠在鐵絲網圍成的圈圈裡,祂們叫著、跳著互相踩踏發出悲鳴爭奪著那些燒成灰燼被風高高揚起金香紙……風更大了祂們數量也越來越多了,祂們在火池內面目猙獰的爭搶、互毆,本來裝在腦子裡的果凍物滴落了、搖搖晃晃的斷肢被扯落了、肚子裡的東西也都流出來了……而祂們好像不覺得痛一樣只是張大了嘴發出風聲般的怒吼和哀鳴。
看到這煉獄般的景象,我簡直嚇瘋了,直覺想要拔腿就跑,但在那沖天烈焰中陡然浮出一張巨大蒼白的臉,那平板如紙的臉上有兩個像是眼睛的黑色窟窿,它們慢動作地環視了空地一圈以後就在朝著我這邊的方向停了下來,大張的嘴巴也像一個黑色的大洞對著這邊露出詭異的笑容……,那個笑容笑著笑著,漆黑的窟窿竟汩汩的流下暗紅色的液體。雞皮疙瘩瞬間竄起、冷汗從背後沁出,我的腳早就被嚇得忘了怎麼移動了。目瞪口呆的我只能裝作若無其事地低下頭看著已經沒了金紙的手,開始在心裡一直重複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的視線緊盯著水泥地面,頭低的不能再低了,卻在這個時候驚恐的發現自己的腳邊居然多了一雙黑色的布鞋!那雙布鞋樸素到讓我懷疑它的年代,眼角的餘光還可以看到布鞋上有一片在昏暗中隨著風翩翩翻飛的藍色裙角,那曼妙的舞姿在火光的映照下卻是沒有影子的……當下我覺得自己的眼眶濕了,在心裡更加瘋狂的大喊:「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法師的誦經聲停了,喊了一聲以後就說家屬可以回去休息了。我想要轉身去拉住媽媽的手,但卻發現黑色的鞋子沒有要離開我身邊的意思。嚇哭的我只能怪聲怪調得喊了媽媽:
「媽,可不可以牽我的手,我……我怕黑。」
「你這孩子現在撒什麼嬌?!」媽媽好氣又好笑的說,但還是伸出手來拉我。一路上我打死不敢抬起頭走路,就這樣盯著墨黑色的路面和身邊的黑鞋,它沒有停歇地一路跟著我進了家門才不見蹤影……我一進門就立刻把自己關進二樓的房間裡面,然後用棉被把自己密不透風的裹緊。也許是太累了,我像喝了安眠藥一樣倒頭就睡。恍惚間我好像夢見了阿公,祂穿著葬儀社幾天前送來的壽衣:一件藍色的長袍、咖啡色的馬褂和黑色的布鞋。阿公在跟一個只有頭的人說話,說著說著祂就脫下原本穿在身上的馬褂披在那個頭的「身上」,那個頭就這樣「穿著」馬褂離開了。剩下藍色長袍的阿公回頭,慈祥的跟我說:
「乖孫,下次母湯卵共話(不要亂說話)啊,阿公咖尬意(比較喜歡)西裝啦,叫你阿爸燒一套來。」
說完阿公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立刻打電話跟葬儀社聯絡,幫阿公訂了一件金光閃閃的紙紮西裝,希望祂穿了以後可以開開心心的去見佛祖。